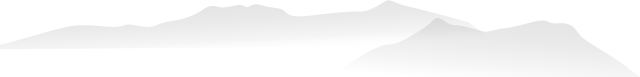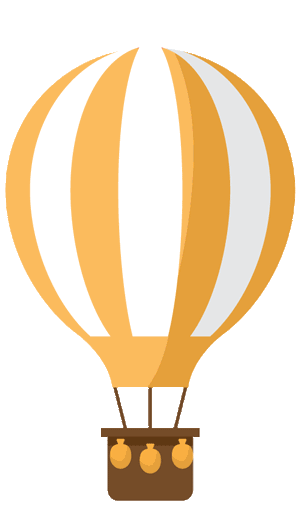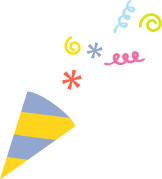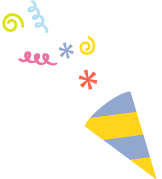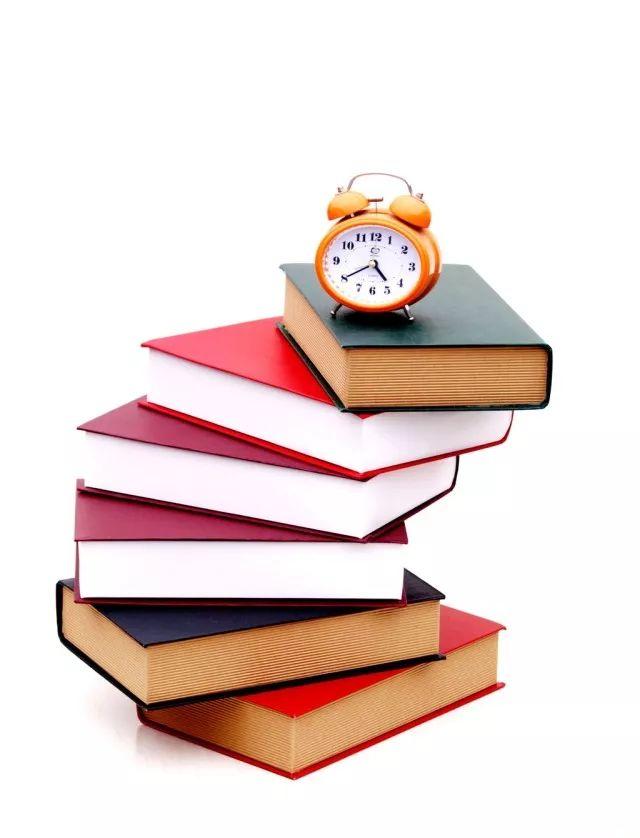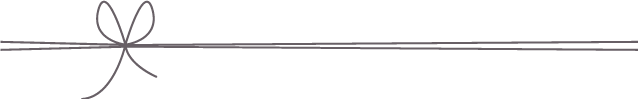主编推介
刘奕伶,女,汉族,四川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兴趣为民间文化、民间医疗等。本文梳理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民俗(学)的论述,并思考了其批判主义民(学)观与五四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呼应关系。
民俗的批判与批判民俗学——葛兰西论民俗
刘奕伶
原文发表于《文化遗产》
2018年03期
摘要: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对民俗和民俗学有过深刻的论述。葛兰西认为,民俗是一种需要进行提升的民众世界观,民俗学的任务是鉴别和批判民众世界观中落后的内容。进而,在其实践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葛兰西的民俗(学)观的分为了三个层面:作为”自发哲学”起点的民俗、以一种世界观为批判对象的民俗学以及民俗学教育在”文化霸权”斗争中的重要性。葛兰西的民俗观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民俗学构成了相互呼应的关系,并为当下的民俗学带来了启发与思考。
关键词:葛兰西;民俗;批判;自发哲学;文化霸权
引子:被忽视的葛兰西之民俗观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1922年,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夺取了意大利国家政权,葛兰西领导意大利共产党展开了反法西斯斗争,于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1937年不幸逝于狱中。
安东尼奥·葛兰西
在监狱期间,葛兰西写下许多的文章结集为《狱中札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狱中札记》中有数篇文章专门论述民俗和民俗学,遗憾的是鲜有民俗学者对其进行深入探究。从大方向上来说,我国民俗学界不乏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观的关注,近年来也有民俗学者考察了葛兰西的思想,介绍葛兰西的民间文学观,或是借助葛兰西关于“常识”的论述,尝试扩展民俗学的范畴。但以上研究比较缺乏对葛兰西著作原文的梳理与分析,也没有将葛兰西的民俗(学)观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呈现出来。美国民俗学者金卡莱拉(Gencarella)对葛兰西的研究比较深入,他系统梳理了葛兰西的民俗及民俗学相关论述,但其阐释没有明确葛兰西观点的价值所在。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填补国内民俗学界葛兰西相关研究的一些空缺。
葛兰西的理论体系十分宏大,我们对葛兰西的民俗观的考察不能脱离其理论体系。因此,先对葛兰西的主要思想进行概观将是有益的。
一、葛兰西思想概观
葛兰西思想的基础是实践哲学(praxis philosophy)。葛兰西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人是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在改变现实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成为人的。而由于人们的实践行为需要一定世界观的指导,因此作为世界观的文化、理论、意识形态也同样重要。实践哲学的重要任务是对旧的文化进行批判,创造新文化,促进社会进步。
由此,在葛兰西的思想体系中,文化占有特殊的地位。早在入狱前的1916年,他就提出了一种与当时实证主义风潮不同的文化观:
我们需要使自己摆脱这样的习惯,即把文化看成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把人看作仅仅是塞满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文化是与此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基于此,葛兰西将文化改造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使他开始思考适用于西方的革命战略。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特殊之处在于市民社会的存在,由此他提出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葛兰西的“霸权”并非指政治支配,而是包括世界观、意识形态、文化等多个层面更广义的支配。霸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且渗透为大众的“常识”(commonsense)。葛兰西提出,“国家”包含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个层次,前者通过强制统治和暴力行使压制性的统治权力,市民社会则通过教会、学校等市民机构行使一种建立在市民同意基础上的文化支配。一个社会集团只有优先夺取文化霸权,才更能保障以广泛认同为基础的政权的稳定性。因此,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
二、作为自发哲学之起点的民俗
葛兰西在《哲学研究》中初步确立了对民俗的定位。文章提出了一个颇具革命性的观点——人人都是哲学家。此处的“哲学”不是指哲学家的一套融贯的思想体系。正如他所说,实践哲学“不可以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和意见的片段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这种大众哲学被葛兰西称为“自发哲学”(spontaneous philosophy),呈现出无系统和偶发的特征,因为它是特定社会集团中的人们身上不自觉携带的知识和世界观。自发哲学必须经过批判才能提升为真正的哲学。
一,语言本身中,语言不只是与内容无涉的语法上的字,语言是既定的观念和概念之总体。二,“常识”(commonsense)和“健全的见识”(good sense)。三,大众的宗教,从而也包含在信仰、迷信、意见、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整个体系里,它们被以“民俗”的名目捆扎为一体。
首先,葛兰西认为语言反映了一个群体的文化要素,可以从语言中估量出使用者世界观的层次。他将语言分为方言和民族语言两个层次,只讲方言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受地域局限,其思想是“经济的—团体的”狭隘地方主义观念;而说民族语言如标准意大利语的人,其思维和认知更开阔,更符合支配世界历史的主要思潮。按照葛兰西的看法,民俗或民间文学同方言一样是地方主义的,因为民俗是地方性的知识和传统,而民间文学则更是与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自发哲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常识”和“健全的见识”。此处“常识”不是指经验知识,而是一般人所持的不成体系的假设和信念。他这样描述常识:
(常识)是“非哲学家的哲学”,是被各种社会文化环境不加批判地予以吸收的世界观……它是哲学的“民俗”(‘folklore’of philosophy),并且像民俗一样表现出不计其数的不同形式。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使在一个个人的头脑里,也是片段的,不连贯的和琐碎的……当在历史上产生出一个同质的社会集团的时候,一种和常识相对立的——换句话说,融贯一致而系统的——哲学也随之产生。
葛兰西用民俗来隐喻常识,说明在他看来民俗同常识一样与系统哲学相对立。但他又说:
每一哲学思潮都留存着“常识”的沉淀,这是其历史有效性的证明。常识并不是某种严格的、不变的东西,它不断改变自身,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自身。“常识”是哲学的民俗,而且总是处于准确地讲是民俗和专家的哲学、科学和经济学之间。常识创造未来的民俗,在一个既定的地点和时间,它是大众知识的一个相对严格的阶段。
常识处于发展中,某一阶段的常识会吸取哲学和科学的内容丰富自身,因此相比民俗而言它蕴含了更多哲学的要素,更接近哲学和科学。
比常识更进一步的是“健全的见识”。葛兰西注意到,意大利人常说“哲学地看待它”,他认为这种表达很有价值,体现出人们思考事物合理性并试图理性解决问题的倾向。他将这种理性自觉的倾向称为“‘常识’中的健全的内核”,认为应当“使之更为一致和融贯”。可见健全的见识比常识又更加接近哲学。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葛兰西的观点中,知识和世界观按照“民俗—常识—健全的见识—哲学和科学”这样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民俗是人们认识的起点和最低点。
自发哲学的第三个方面是“大众的宗教”,那些被称作“民俗”的与宗教有关的迷信。葛兰西认为宗教是分层的,普通民众的宗教与上层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可以宣称,所有宗教,即使是最精细最复杂的宗教,对于现代思想来说都是’民俗’,但本质的不同在于,以天主教为首的宗教是由智识阶层和教会阐述和建立的。”存在于大众宗教中的是一种“民众的道德准则”,它是广大民众行动的纪律和习俗的依据。大众宗教的道德准则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来源于过去的生活,比较保守和反动,即民俗和迷信;另一种则与常识相似,自发地吸收了进步的思想进行了革新,例如欧洲历史上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运动。
葛兰西认为民俗是自发哲学的起点,他曾相当尖锐地直言民俗是“最低层次的大众文化”,亟待批判和提升。但这并不代表他轻视民俗及其相关问题。
三、民俗学是关于一种世界观的学问
葛兰西没有给民俗下定义,因为他认为将某些事物归为民俗这种分类式的认识和研究是不可取的。在《对民俗学的观察》中,葛兰西对当时意大利以搜集、分类、评鉴为主的民俗学研究提出了意见:“直到现在民俗主要还是被当做一种’古雅的’元素来研究。”葛兰西认为,民俗是一种与官方世界观相对立的世界观和生活观,所以民俗学应上升到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层次。这与他反对“百科全书式”的实证主义文化观相符。
接着,他探讨了民俗作为世界观的特性:“这种世界观是不周密的和不成系统的”,因为底层民众没有能力掌握一种精心构架的观念系统。每个新的社会集团都会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但并不是一旦新文化出现了,就立刻会被所有阶层接受:“在新的社会集团的各阶层中,存在着特色各异的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阶层还仍然沉浸在先前历史情境的文化(有时也包括那种直止最近才被取代的文化在内)之中。”民俗就是保留了这些先前历史情境的文化要素的“活的证据”:“民俗是民众文化生活状况的反映,就算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或被修正了,相关的民俗还是被保留下来,或是与现有状况相结合形成一种古怪的混合物。”
所谓与现有状况结合,指民俗保留旧文化也吸纳新文化:“哲学与现代科学在不断地为‘现代民俗’(modern folklore)贡献新的元素,特定的科学概念总是被从它原本的语境中移入民众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或多或少的歪曲,嵌入传统的镶嵌画中。”他举例道:一位意大利吟游诗人写了一首方言诗赞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发现新大陆本应是属于全人类的科学壮举,但这首方言诗仅仅指向意大利人的智慧,反映出一种保守的“大众沙文主义”(popular chauvinism)和狭隘的地方主义情感。
葛兰西评述了当时一种对民俗的称呼——“当代的史前史”(contemporary pre-history)。他由这一称呼联想到了“次级艺术”(minor arts)和“主流艺术”(major arts)的区分。次级艺术总是依附于主流艺术,主流艺术的创作者是创造性的艺术家,而次级艺术的创作者只是工匠。葛兰西将次级艺术与民俗类比,民俗总是依附于统治阶层或智识阶层的文化,从中获取一些母题,将之嵌入保守的传统框架中,因此,“没有什么比民俗更矛盾、更碎片化了”。
从民俗的以上特征出发,葛兰西继而对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提出了质疑。他说:“没有什么比试图从单一区域的民俗中理出不同层次更徒劳了。然而就算是将不同地区的民俗进行比较(尽管比较是唯一具有方法论价值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只能得到一些可能的假设,因为当人们比较民俗时,其实比较的永远是一个混杂了各种成分的实体。要写出关于各个地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绝非易事。”葛兰西没有点明,但可以看出他指的正是历史-地理学派的比较研究法。
正是由于民俗复杂的特性,葛兰西才会强调:“民俗学研究的核心应该有所变化,在宽度和深度上都应有所拓展。民俗不能被看做一种奇异事物或者一种古雅的要素,而应该被看做是一种严肃的事物加以严肃的对待。”对民俗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收集、审美和比较层面,而是要像将它作为一种民众的世界观加以批判,与文化研究以及文化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
四、文化领导权斗争与民俗学教育
至此,葛兰西对民俗的看法似乎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民俗是依附性的底层文化,是与现代科学和哲学相对立的一种世界观,亟待批判;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关心民俗学,强调民俗研究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既然民俗是落后的,为何不干脆主张废除民俗学呢?这是由于,民俗是文化霸权斗争中的重要一环,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
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上台。自1923开始,墨索里尼手下的教育部长实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减少了学校中的民族语言教学,并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加入宗教教学。葛兰西极力反对这种教育方针的,认为这将导致民众的世界观难以从民俗和常识的层次得以提升,这是法西斯政权为保证对民众的控制而实施的一种计策。
在《寻求教育原则》一文中,葛兰西探讨了他的教育主张:在学校中强化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把儿童培养为市民社会的合格公民。作为葛兰西教育方针所强调的“科学”的对立面,民俗是应当在教育中被取缔的内容,他说:“儿童所学到的科学思想与他们从渗透着民俗的环境中所吸收的对世界与自然的神奇看法相冲突,而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则与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野蛮行为(民俗的另一方面)的趋势相冲突。学校在同民俗作斗争,实际上在同传统世界观的一切残余作斗争。”由于耳濡目染,人们很难对民俗产生清醒的批判意识,因此经由教育系统与民俗世界观作斗争,是培养新人和新文化、从法西斯政府手中夺取文化霸权的必然要求。
但葛兰西并不主张在教育中根除民俗学。他在文章中引述并赞同了齐亚皮尼(Ciampini)在师范学校中开设民俗学课程的主张,但他认为齐亚皮尼混淆了一些问题,没有厘清“关于民俗的科学”(science of folklore)与“民俗知识”(knowledge of folklore)、“民俗”(folklore)与“民俗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folklore)之间的关系:“对于齐亚皮尼而言,民俗学(即民俗学研究)就是目的本身,或者说,其唯一的功用在于向民众提供进一步认识自己的因素。研究迷信的目的是为了铲除迷信,这在他看来不啻是民俗学的自杀,因为科学不过是客观的认识,是目的本身!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师范学校开设民俗学课程呢?为了向未来的教师们灌输客观的文化知识么?向他们展示哪些东西绝对不能被毁掉吗?”教师接受民俗学教育不是为了了解各种民俗事象,而是要在把民俗作为一种世界观来了解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针对教师的民俗学教育,目的在于使教师了解哪些观念对年轻一代的智识和伦理产生影响,以便用更先进的观念来替代它们。
可惜现实与葛兰西的期望背道而驰。1929年开始,法西斯政府对民俗学相关工作展开了管控。法西斯政府宣扬意大利民族意识,将民俗当做法西斯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意大利的民俗学者助纣为虐,尤其是那不勒斯大学东方民族学研究所的教授科尔索(Corso),他极力宣扬“民俗是一个民族至高无上的传统,不尊重传统就是摒弃自己生命”,帮助法西斯政权传播膨胀的民族自豪情绪,使民众也陷入一种狂热蒙昧的状态。
五、余论
葛兰西具有启发性地将民俗看作一种世界观,避免了我们在定义民俗时常常陷入本质主义想象,赋予了民众一种能动性和主体性,因为世界观具有提升的可能。同时,葛兰西的民俗观是批判的。他认为民俗具有历史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保留着过去的痕迹,包含着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民俗学应当对这些内容加以辨别和批判,而不是陶醉于民俗事象中。
回顾历史,我们将看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脉,孕育了中国民俗学的歌谣运动其实也有着批判的色彩。比如常惠与刘经菴在歌谣运动中研究歌谣与妇女问题,刘经菴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的家庭,向来是主张大家族制的;因之妯娌与姑嫂间的倾轧,婆媳与夫妇间的不和,随处皆是,无家不有……妇女们总是幸福之牺牲者。中国歌谣关乎妇女问题多,恐怕就是中国家庭不良之明证了。
而周作人在评价刘经菴的研究时则说:“这是一部歌谣选集,但也是一部妇女生活诗史,可以知道过去和现在情形——与将来的妇女运动的方向。”以歌谣来批判社会、指导运动,中国民俗学有着批判乃至革命的底色。而在当下,批判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词汇。但正是在这种现状下,葛兰西的观点显示出其价值,因为它促使我们反思——只要是从民间来的东西就值得我们为之欢呼雀跃吗?任何民俗事象在当下都是对民众有益的吗?民俗学者需要肩负起启发民众的社会责任吗?
我们也可以探寻葛兰西民俗(学)观与中国民俗学的批判传统背后更深层的东西。葛兰西提倡改造民俗世界观,最终目的是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文化霸权。而在中山大学领军民俗学运动时,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学者高举革命大旗,将民间文学视为教育民众、拯救国家的利器。尽管二者对民俗和民间文学有着不尽相同的评价,但共通点在于都将它们视为介入实践、实现革命目标的手段。与这种激进的、革命的观点相对,歌谣运动中,还有一些学者更加强调民间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学术价值,周作人和胡适可谓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两种观点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始终处于分歧而又交织的状态。在1925年为刘经菴《歌谣与妇女》所作的序中,周作人提到当时民间文学研究有三种方法,一是将民间文学视作风俗调查的资料,进行文化史的研究。二是诗学研究,将歌谣“当《诗经》读”。三是像刘经菴这样,“从歌谣这文艺品中看出社会的意义来”。前两种研究方法分别对应《歌谣周刊》发刊词所说“学术的”和“文艺的”目的,第三种则是更为激进的研究方法。刘宗迪曾谈到,歌谣运动初期强调学术的和文艺的目的,但由于其深刻的民族主义背景,在后来的研究中,为文艺的目的基本上被悬置了,只有胡适一直坚持就文学论文学。岳永逸新近关于李素英的研究也展现了歌谣运动以来两种民间文学研究的冲撞与调和。他总结,歌谣除了审美的精神性之外,还被赋予政治性和革命性,当价值理性占上风时,歌谣形而上的审美价值就得以强调,当工具理性占优时,则更强调歌谣经世济民的效能。
激进的民俗学与审美的民俗学,谁占上风往往是时代的选择。葛兰西批判的民俗(学)观,也是他观察意大利历史与现状的结果。今天的重点是二者如何把握、调和。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民俗学在发挥民俗学的公共性与启发教化作用时,应警惕陷入文化民族主义和忽视民众主体性的文化政治学。也有人呼吁,当下中国民俗学应当适当回归文本,重视民间文学作品的批评研究。民俗和民俗学作为促进社会变革、教育民众之工具的限度在哪里?民间文学研究如何回归“为文艺”的初衷?都是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问题。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欢迎投稿
栏目主编的邮箱:
yunafk929@163.com
公号公共邮箱:
folklore_forum@126.com
(这个邮箱请注明新青年)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18年03期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拓展阅读
58.新青年 | 程浩芯:还俗于民:本杰明·博特金与美国民俗学的公共性实践
57.新青年 | 张倩怡:“梗”与“玩梗”:ACG亚文化群体的口头文类及实践
56.新青年 | 王维娜:“有情”与“无情”:长汀客家山歌主题研究
54.新青年 | 崔若男:手帕姊妹:明清江南地区娼妓结拜习俗研究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中国民俗学会 · 业务范围
理论研究 学术交流 业务培训
书刊编辑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中国民俗学会
微信号 : ChinaFolkloreSociety
微信订阅号:民俗学论坛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民俗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