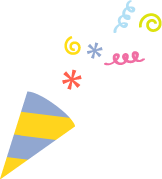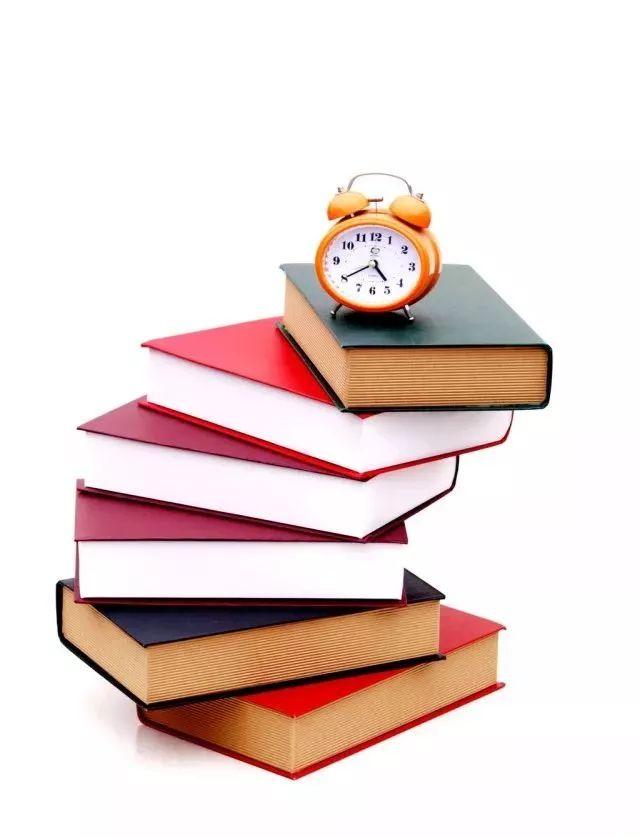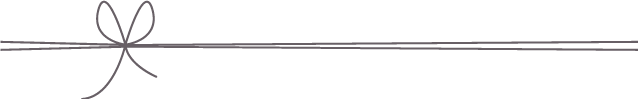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石圆圆,女,汉族,江苏宜兴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和东亚地方文化。本文通过对宫本常一田野调查的分析,探究乡土书写的“诗性”之辩。
乡土书写的“诗性”之辩:从宫本常一的田野调查谈开去
石圆圆
原文发表于《文汇报》“文汇学人”专栏
2017年8月
宫本常一作为一位民俗学者,在20世纪的日本文化史中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他被人熟知的行者一般的田野记录生涯,他对日本民俗学中民具学的开掘之功,以及堪称专业水准的摄影作品,这一切都为宫本展示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在当代日本,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众社会,宫本仍然获得广泛的认同。他对日本,尤其是对战前日本乡村的基础而切近的描述,几乎接近一种带有浪漫主义性质的日本人论,将他和其他学院派的民俗学家区分开来。
宫本常一(1907-1981),日本民俗学家。代表作有《被遗忘的村落》《栖居于山间的人们》《庶民的发现》《民俗学之旅》等。
20世纪是民俗学在日本得到迅速繁荣的时期。从上半叶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崭露头角并确立其学说系统,到后半叶民俗学流派的多元发展,民俗学对日本人的自我认知和文化发展的类型,都起到了稳定和推进的作用。在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城乡变革和迁徙的浪潮中,民俗学所展开的广泛的讨论视域,对日本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在经历了政治经济几次急剧动荡期的日本,传统文化得以较好保持的重要原因。
宫本常一出生于1907年,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行日本山村的田野调查,一生徒步考察16万公里。他著作甚丰,于六七十年代集中出版,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山民和岛民的记录。相对于新兴发展的城市,宫本的落笔之处在于乡村,正如他的家乡,包括逐渐退出主流生活的偏远的“未开化”地区。他对农民生活的细致考察,涉及生产方式、政治生活、文化传承各个方面,笔者认为,宫本常一最了不起的书写特点,在于这些方面多是通过动态生活场景的描述而表现出来的。
宫本常一的田野调查代表作《被遗忘的日本人》在2017年初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中译本名为《田野调查:被遗忘的村落》。受恩于郑民钦老师的优雅译文,更多的中国读者得以了解这位民俗学家的存在,以及他笔下的那个“无名”的日本乡土世界。2010年此书在美国的英译本问世时,也曾引起不小反响。我们被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乡土环境中的鲜活的生命体验所感染,关于一个农民的个体成长史,关于家族和家族以外的伦理关系,关于男人、女人和亲子,关于人和村庄以及养成他们的时代。在这些浸润着山风和海盐味的记述对象身上,可以真切地看到山,看到海,以及宫本常一与这些词句和场景交互的热情和彼此产生的鼓动。这样的“诗情”如何生成,宫本常一和对象是何种书写关系,以及这种“诗情”在当代的语境中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变动中的乡村,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命题。
首先是“移动”。这个“移动”不是指作者的旅行写作,而是指被采访对象的辗转漂泊的历史。《被遗忘的村落》中描述了大量的农村流浪者形象,这在当时并不是民俗学农村考察对象的主流。《流浪者的谱系》《世间师(一)》《世间师(二)》《土佐源氏》是专篇写农村漂泊者的,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零星叙述。在《流浪者的谱系》的开场白里,宫本说道“除农耕社会之外,大多数民众不是都在移动吗?其中有的人有一定的据点,有的人如无根的浮萍般移动。在日本,浮萍般的流浪者很少”。大部分是以流浪为生活手段的人,也就是说,流浪是伴随经济活动而进行的。但中间也有不同的层次,有因个人际遇而流浪的人,也有因工作(生产)方式而流动的人。在《谱系》一文中,作了海上漂泊者、山间漂泊者、山中行者、落伍者群体等的区分,他们中包含了渔民、猎人、行商、手工艺人、流亡乞丐等,作者分析了他们旅行的动力,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还涉及“流浪信仰”。值得一提的是,在另一篇并不是流浪主题的文章《女人的社会》中,讲述了乡村年轻女性的移动。姑娘们流行在婚前结伴旅行,拿着很少的盘缠,有的纯粹是游玩,有的去异地工作,有些人和途中结识的旅伴情投意合嫁到了他乡,当然也有离家出走的少女,大部分的人都会回来。她们把这种旅行作为学习的“舞台”,可以“掌握家乡人所没有的知识,以此自豪,其中之一就是学会外地语言”,虽然艰辛,却让人尊敬。因为当时(按文中讲述老者年龄推断大约是十九世纪晚后期)的人们认为“要是姑娘不懂得社会,就没有人娶她。因为她只知道家里的规矩,不了解社会,想事情就会很狭隘。”不禁让人想到一千年前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女性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一书中所写的“女人的前途”。清少纳言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家庭,应该尽量让女孩子学文识字,甚至离开家庭去出任宫里的官职,这一切,皆是为了“学习观看世间的方式”。虽然在文末也一笔带过这对婚姻的益处,不过清少纳言是很幽默地做了给家人增加颜面的解释。一千年后日本贫穷村落少女的旅行,和平安时代贵族女孩的出仕,本质大约十分相似吧。这样的洒落和见地,并没有因为阶层差异而出现偏差,也非孤立在性别语境中产生,似乎穿越了时空,其中呈现的智慧,堪称潇洒,恐怕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
宫本常一摄影作品
宫本常一笔下的流浪者,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作者从来不把观察对象当做经济关系中一个结构性的存在,而是通过对其言行回忆的转述,把“人”的主体性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比如土佐源氏,一位真正的流浪贫民,没有因为落泊而失去话语的权利,恰恰相反,相信读者对他的成长罗曼史印象颇为深刻,宫本常一将无数温柔笔墨赋予这位一生挚爱着女人和牛的乡村落伍者,让他说出了“我骗了不少人,但没有骗牛”、“其实每一个都是亲切温柔的女人”之类的名句。宫本承认在闭塞的世界里存在着不可称颂的盲区,但受到环境制约的人们也对应生出自己的法则;并且,这个浑厚世界中的文化积淀是错层的,也是多元的。除了农村边缘人,他在文化传承者方面的记录更为用心。
作者自己说明,这本田野调查的主体之一,是写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古老传承,即描述这些老年人年轻时是在何种环境中如何生存下来,“不是作为单纯的回顾,而是作为与现在密切相关的问题,思考老年人产生的作用”。《文化传承记录者》系列几乎采用了摄像般的密集采写。尤其是第二篇,把与高木诚一的交往细节一一交代,让高木的博学、技巧和视野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写出了一位“向村民展示着思想和生活的方向”的文化传承者形象。宫本用最尊敬的语言表达了对他们的评价:“民间的文化传承者不仅仅是单纯地将旧传统传承给后代,还为改善自己的生活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努力。……这其中闪耀着农民的朴素和充满活力的明朗……正是以他们为核心的一群人,引领着战前的日本农村走向进步。”

农人插秧
通过高木诚一的背景和支撑体系,可以看到宫本常一民俗研究的社会时代背景,这是十分重要的切口。高木的乡村体验和研究是十分全面的,涉及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宫本常一的工作其实也是如此。但宫本强大的视觉感官系统,以及敏感的心性,使他的书写不再拘泥那一种风格,而是趋向和讲述者立场融合的视角。若非有真正的共感和同情,是无法做到的。《我的祖父》一文通过对祖父宫本市五郎的人生追忆,实则揭示了宫本常一的成长背景和民俗启蒙,为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他的民俗书写立场提供了注释。作者并没有写祖父是如何教他说唱民间口头文学,只是平静地叙述了和祖父一起生活的时间里所听到看到的琐碎片段。其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和祖父一起试图救助一只乌龟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是宫本常一乡土启蒙的缩影,也体现了他乡土观的核心。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山里田边的小水井里有一只小乌龟,我每次上山都要看一眼这小乌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想总困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很可怜,就让祖父把乌龟从井里捞上来,用绳子捆着拿回家去,打算在家里饲养。我高高兴兴地往家走,但路上忽然觉得乌龟很可怜,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定会感到很寂寞。我手提着乌龟大哭起来,一个路过的女人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只是说“乌龟很可怜”,继续往山上的田地那边走去。那女人跟着我走。在田头,祖父安慰我,要我把乌龟放回水井里。他说:“乌龟有乌龟的世界,还是放在这儿好。”我现在还记得这句话。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这只乌龟还在那口井里,而且长得很大了。有一天,旁边田地的老大爷说:“乌龟长得这么大了,那里面的世界太小了。”然后把他捉上来,放到旁边的溪涧里。傍晚我沿着山路回来,有时看见乌龟慢吞吞地在路上爬。祖父只要在山路上看见这只乌龟,回来后肯定都会告诉我。
珍惜着自然中人和动物一切生命,让生命在适宜它的环境下生长;也不固执地拒绝改变,墨守环境,而是随着自身的发展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世代之间的心灵交流是传承的途径。关于祖父的记忆,糅合了睡前的童谣、草子传说、生活禁忌、节日礼数,以及从“我”十岁开始每晚祖父都用苍劲的嗓音领唱的“口说”表演。这是祖父最擅长的表演,也是他一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民俗印记。这类口说文学,其表演的趣味性和仪式感要比说唱内容本身来的更重要,而且由于音调、说唱习惯的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表演都有自己的特点。正是因为有所不同,才是真正的人的传承。这段经历是宫本常一的起点,故乡也成为他后来研究的重镇。他从来都不是要努力去成为“他们中的一个”,而是他从未把自己“置身于外”。作为民间传承者和记录者,宫本常一背负了和祖父不同的使命,却始终忠实于从祖辈那里习来的关于存在和自然的法则。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本里充满了身体的经验。这个身体所在之处,便是他的立场。
在宫本常一的镜头下的田野和农人,很美。和他呵护乡村的文字一样,是一种温情的注视。在熟知乡村种种生态的前提下,在追求村落繁荣的愿景下,这种温情并不是和政治历史语境相隔离的感伤,不仅来源于血液中流淌的故土情结,也包括对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一种生活终将成为历史的预知,体现了对残留在这块背景中的人物的切身的体恤。真正改变的不是土地,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文化和民俗的传承,对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详尽记录,恰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们了解自我,认可自我,有可以回溯的文化故土和心灵栖息之处,由此获得可以继续前行的力量。从这个视角来理解,可以说宫本常一的田野调查和民俗写作,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时代日本的乡土情感结构。
田野调研现场
尽管在当代的城市生活中,对故土的情感需求似乎已经不那么迫切,那这种诗情是不是一种梦幻的片刻满足呢?具体的民俗形式,也许会在文献和博物馆中保留下来,而人们的主体情感,则活态地蕴藏在每个人的记忆之中。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的,“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而“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这是文化传承的历史基础。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乡土不当作乡村实体,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文化体系来阐释;此时乡土不是故乡和某个具体的村落或者地区,而与民族国家同构。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如何将个体的历史和民族记忆相关联,捕获完整的历史感和文化体验,以期创造更为丰富的当下和未来,也许可以从用心记录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开始,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
欢迎投稿
栏目主编的邮箱:
yunafk929@163.com
公号公共邮箱:
folklore_forum@126.com
(这个邮箱请注明新青年)
文章来源:《文汇报》“文汇学人”专栏,2017年8月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拓展阅读
50.新青年 | 陈粟裕:丝绸之路与“蚕种东来”(内含日签)
49.新青年 | 梁青:当代日本民间叙事研究的走向(内含日签)
46.新青年 | 李斯颖:壮族蚂拐节仪式起源神话的探析——从盘瓠型“龙王宝”神话说起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中国民俗学会 · 业务范围
理论研究 学术交流 业务培训
书刊编辑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中国民俗学会
微信号 : ChinaFolkloreSociety
微信订阅号:民俗学论坛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民俗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