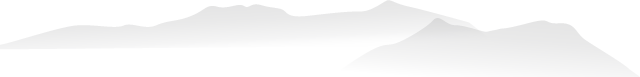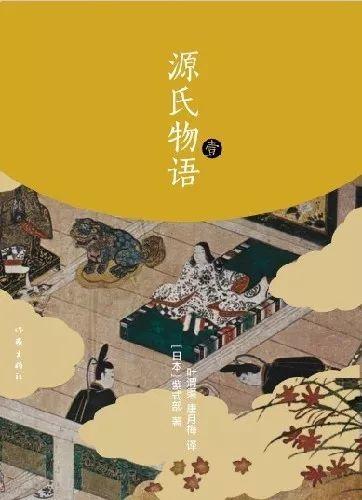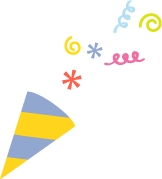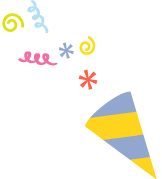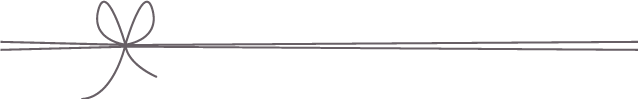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梁青,男,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现为湖北大学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神话学、中日比较民俗研究、中日比较神话研究。本文对日本民间叙事研究作出概括与爬梳,弥补了中国学界重视日本民俗学而不重视其民间叙事研究的缺憾,是为要文。
当代日本民间叙事研究的走向
梁青
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03期
摘 要:近代以来对民间叙事的研究率先在欧美发展起来。叙事学确立后,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影响下,民间叙事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本学界紧跟学术潮流,积极引入民间叙事理论,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日本民间叙事研究者在引入西方新理论时注重与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对新理论有选择有取舍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民间叙事研究;叙事学理论;理论应用;学术传统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史,受日本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这一方面是所谓的“同文同种”在语言上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是日本在近代以来开西学风气之先,率先将西方理论消化,让文化体质相近的我们更容易接受。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化浪潮的不断冲击,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都可以更快更直接地引介进来。我们在引入西方理论方法的速度上和数量上与日本的差距正在缩小,有时甚至超过了日本。相比对西方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对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学术界失去了借鉴的价值。相反,随着我们引进西方理论速度的加快,产生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理解偏差等消化不良的症状,日本的译介经验和方法对于我们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从正式建立至今仅有大约半个世纪,“叙事学”一词甚至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洛夫提出。但人们对民间叙事进行研究的历史却久远得多,雅各布·格林的《德国神话》(1835)是近代民间叙事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从此人们开始按照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等体裁,把民间叙事作为口头艺术的形式进行考察。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学者们对神话的研究日益兴盛,在欧洲形成了一股国际风潮。这一时期,恰逢日本明治维新,学界以开放的姿态引进西学,神话研究之风从西方吹进了东方世界,井上圆了、清野勉、高木敏雄等一批学者奠定了日本神话研究的基础。当时中国的留日青年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蒋观云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一文,首次将“神话”概念引入中国[p149-154]。可以说,我国近现代的民间叙事研究是由日本东渡而来,继而走向繁荣的。
民间叙事研究在近代以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新思潮和新理论。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以来,民间叙事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意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长期以来,民间叙事研究理论的中心都在欧美地区,这种状况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难以改变。一直以来,中日两国的民间叙事研究对西方的理论方法多有借鉴,我们在吸收和运用西方民间叙事理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移步扶桑,看看老邻居是如何应对的。
一、经典叙事学视域下的当代日本民间叙事研究
芬兰学者Kaivola-Bregenhøj.A将民间叙事学的历史进程依据研究对象划分成三个阶段:叙事、叙事者和叙事活动[p208-214]。日本学者们的研究路径也大抵如此,他们一开始专注于叙事文本,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甚至神乐、祈词等,然后才将目光投向叙事者,关心他们的生活经历,继而关注叙事的语境和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经典叙事学的确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里我们把受经典叙事学影响及其以降的研究称为当代民间叙事研究。但就研究对象而言,仍然可以参照上述的三个阶段。
(一)对叙事文本的研究
传统的民间叙事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文本的考察上。无论是对文本体裁的界定,还是关注文本在时间、空间上的变异,或者是母题和类型索引的编订,都是着眼于文本的内容的。到了当代,受经典叙事学的影响,日本民间叙事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关注文本的结构规律和形式问题。
这方面的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广田收的『物語りにおける伝承と様式』[p36-47](物语的传承和形式)。广田认为古代物语和神语(神敕)一样,是神圣性的显现,具有对称的形式和循环的构造。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对《伊势物语》第六十段、第六十二段和《源氏物语》花散里卷的结构进行分析,表明它们是同源的并具有相同形式的文本。此外还有繁原央的『日中説話の比較研究』(中日故事的比较研究),谷口广之的『軍語りの様式と構造』[p48-58](军记物语的形式和结构);谷口卓久的『「竹取物語」の潜勢力:<始まりの>様式』[p59-68](《竹取物语》的潜势力:<开始的>形式)等诸多成果。这些成果大多关心叙事文本在形式上的特征,大量采用结构主义方法,其运用也比较纯熟和自如。
在众多叙事文本的研究中,除了大量关注结构与形式的成果外,还有几类研究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日本特有的叙事文本体裁界定问题。叙事文本体裁的界定是传统民间叙事研究的经典问题,在我国一般界定为神话、传说和故事三类。但日本的情况比较特别,有神话、昔话、传说、世间话、物语等多种说法,需要进行区分。这方面值得关注的是长野晃子的『世間話は伝説・昔話・神話とどこが違うのか』[p2-7](世间话与传说、昔话、神话有哪些不同)、『民話の枠分類――昔話、世間話、伝説、神話の語り方の違い』[p17-19](民话的分类——昔话、世间话、传说、神话在叙事方式上的区别)。前者主要是以日本特有的“世间话”为话题,论述其与其他几种体裁的差异,认为其具有交际功能。后者则是从叙事方式上对几种体裁进行区分。
二是对口述和文本之间的转换问题的关注。这个问题在日本学者中的关注度较高,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兵藤裕己的『座頭(盲僧)琵琶の語り物伝承についての研究――文字テクストの成立と語りの変質』[p101-207](关于琵琶法师(盲僧)叙事传承的研究——文字文本的成立与叙事的变质),福田晃的『語り本の成立:台本とテキストの間』[p54-64](语本的成立:唱词与文本之间),以及岩濑博的『伝承文芸の研究—口語りと語り物—』(传承文艺研究—口述与文本—)。前两篇都是对琵琶法师的唱本进行考察,其中兵藤裕己对多个琵琶法师的唱词和师承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在明治初年以前的唱词比较自由松散,琵琶法师们往往在核心情节的基础上自由发挥,琵琶的弹奏也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明治时期唱词逐渐被文本化,还进行了分段分节,于是每段唱词声音的大小、高低、速度和音调都被固定下来,整个表演也与之前发生了很大的不同。福田晃的研究集中在关于《平家物语》的一个唱本上,通过对其历时性梳理,发现镇魂风俗的固化使得唱词被固定下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整个研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岩濑博则是对从总体上对口述与文本在传承上体现的特征进行了综述。
三是对少数民族民间叙事的关心。日本唯一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虽然人口很少,而且没有文字,但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口传文本,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从民间叙事角度展开的研究有大喜多纪明的『樺太アイヌの口承文芸における語りの構造:浅井タケのトゥイタㇵ「カラスと娘」の場合』[p69-78](桦太阿伊努口承文艺中的叙事结构:以浅井タケ的トゥイタㇵ“乌鸦和女儿”为例),以及远藤志保的『アイヌの祈詞における語りの特徴』[p83-101](阿伊努祈词的叙事特征)。前者是用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方式,抽取了“乌鸦和女儿”中的四组共七对互相对应的交差对句,阐明了这个异类婚故事的结构。后者考察了祈词中的语言表达形式,并对比英雄叙事诗和日常生活话语,认为祈词和英雄叙事诗类似,其语言表达形式和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属于雅语范畴。
从以上几类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对叙事理论的运用较为灵活,在日本特有的叙事体裁、叙事方式、叙事语言上都能很好地运用。
(二)对叙事者的研究
在世界范围来看,对叙事者的研究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他们并不是与研究者处于共同完成研究的平等地位上。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个性往往被忽视,常常被当作人云亦云的复述者。但当民间叙事研究的焦点从文本转移到叙事者身上时,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根据Kaivola-Bregenhøj.A的归纳,当代民间叙事研究中,对叙事者的这样几个特点比较重视:叙事的创造者与讲述者不必是同一人;叙事者体现一种集体性的口头传统;叙事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叙事者的故事并非一次性产品;叙事者具有不同的个性[p208-214]。对叙事者的研究为学者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日本的民间叙事研究者们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踏入这个新领域。
日本学者广泛开展对叙事者的研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野村纯一在1983年出版了专著『昔話の語り手』(故事的讲述者),虽然只是对那些讲述人进行了总结分析,但他已经意识到讲述人的存在和他们的重要意义了。其后有广田收的『伝承者の系譜 物語りの話者の位相』[p241-265](传承者的系谱 故事讲述者的存在方式),金子明雄的『語り手とは何か』[p67](讲述者是什么),武田正的『東北地方の語り手』[p296-324](东北地区的讲述者)等成果。这些研究普遍关注叙事者的状态、身份等问题,体现出学者的人文关怀。不仅是对故事讲述者,还有对祭祀活动参与者甚至演艺的表演者的研究。如铃木正崇的『神楽と鎮魂-荒神祭祀にみる神と人』[p93-137](神乐与镇魂—蛮神祭祀中的神与人),『神楽の中の巫者』[p351-376](神乐中的巫者)以及『神話と芸能のインド―神々を演じる人々』(神话和艺能的印度—扮演神明的人们)。铃木的研究中注重了各种身份的叙事者在神乐叙事中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除了叙事者的状态、身份,还有学者注意到叙事者是如何成为叙事者的问题,开始考察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例如高木史人的『昔話伝承者とその生活史』(故事传承者和他们的生活史),还有高桥雅也的『都市的経験のナラトロジーに向けて―戦争遺産の語り部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p153-166](面向都市经验的叙事—战争遗产的叙述者们的生活经历)。这里前者是以弄清故事传承者产生过程为目的的考察,叙事者们讲述的是祖辈们那里流传下来的故事,而后者则聚焦到战时体制下的“花冈事件”的主体,他们是秋田县花冈矿山“花冈事件”的亲历者,为了承担讲述历史事件的主体责任,进行的以保存记忆遗产为目的的讲述,叙事者们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
还有一部分学者注意到听众具有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有齐藤征雄的『語り手と聞き手の物語』[p93-104](讲述者和听众的故事),以及武田正的『民話(昔話)の語り手と聞き手』(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与听众)。他们把听众放到叙事者对等的位置上,认为听众和叙事者共同完成了故事,听众的缺席会造成故事的不完整。
与我国相比,日本学者对叙事者的研究面更宽,关注的群体较为广泛。但对具体的个案研究尚不深入,还没有看到关于某个故事家的研究,也没有对故事村(群落)的研究出现。
(三)对叙事活动的研究
随着对民间叙事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叙事活动,也就是传统生活自身。在西方,这一风潮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在日本则大约始于九十年代初。叙事活动包含的内容很多,涉及到空间、时间、身体的动作行为、声音、叙事技巧(策略)等,这些要素在美国民俗学界主要体现为表演理论,但日本学者仍然倾向于将这些要素分开探讨。
关于空间与时间问题,有永池健二的『「うた」のある風景―歌の場・歌の時・歌のかたち』[p115-126](有“歌”的风景—歌的场·歌的时间·歌的形式),以及高木史人的『昔話の<場>と<時>』(故事的“场”和“时”)。两者都把目光放在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叙事的环境上,认为环境对叙事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于身体的动作行为和声音,日本学者成果较为丰富。有兵藤裕己的『声と主体——モノ語りの語り手と地霊の信仰』[p19-28](声音和主体——故事的叙述者和地灵信仰),以及『「口承」Oralityということ——声、ことばの身体性』[p158-164](所谓“口传”Orality——声音、语言的身体性)。前者关注声音与其主体的关系,认为叙事者一方面是声音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又是地灵这个主体的声音。后者则集中考察口头文学中的声音,把它作为身体行为的一部分进行分析。此外还有川村清志的『民俗芸能の習得と実演における言葉と身体、そして意識についての断章』[p28-32](民俗艺能的习得与表演时的语言、身体以及意识)讨论了叙事活动中语言、身体和意识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以舞蹈等艺能为研究对象的吉川周平,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舞蹈动作的文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仅仅关心舞蹈的核心动作[p3-10],后来他发现舞蹈动作具有结构特征,进而发现动作中隐藏的意义[p56-59,p141-146],总结出一套观察身体动作的分析方法。这类研究在其他地区是很少见的。
关于叙事技巧和策略,主要涉猎者是文学和语言学专业方向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不限于民间叙事,大多数都是面向所有文本的宏观论述和关于作家文学的研究,这里举出一些与民间叙事有关的研究。如高桥亨的『歌の技法と物語の技法』[p315-336],水野隆一用英文发表的『Revealing but Concealing: the Narrator’s Tactics in the Abraham Narrative』[p1-11](揭秘隐藏在亚伯拉罕叙事中的叙事者策略)。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学术背景,虽然研究对象是民间叙事,但研究方法往往是作家文学或者语言学的。
相比以上这些叙事者活动各个要素的研究,日本学者对美国民俗学界一度热捧的表演理论反响不大。除了一些教育学的学者试图将表演理论运用到教学工作以外,只有桥本裕之和小长谷英代等学者在谈到博物馆展出中的展示问题[p537-562],以及梳理民俗研究的传统时[p171-177]对表演理论有所论述。
在经典叙事学的影响下,日本当代民间叙事研究者们逐步接受了西方叙事理论,从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上都能与西方接轨。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生搬硬套和滥用,在大量的民间叙事研究成果中,上面列举的只是运用这些理论产生的成果,还有大量传统方法和理论指导下的研究。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对日本特有的一些状况,日本学者们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最大限度规避了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
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方法在20世纪末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冲击,西方叙事理论又迎来了新的浪潮。日本民间叙事研究也因此有了新的动向。
二、日本民间叙事研究的新发展
叙事学成立以前,叙事研究的主要领域在民间文学。作为叙事学理论重要来源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可以说都是在民间文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在语言学的帮助下,叙事学一经成立,便脱离了民间文学的怀抱,走向了更广阔的领域,虽然也偶尔回到民间文学的土地上,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作家文学中发光发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间叙事理论与叙事学的关系发生了转换,特别是后经典叙事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之后,叙事学对民间叙事理论的引领作用越发明显。呈现出叙事学追随语言学,民间叙事理论追随叙事学的样态。
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呈现出五个新的发展向度,即语用学转换、意识形态的介入、女性主义、向新媒介渗透和认知论转向。这些新的趋势已经或者将要对民间叙事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看到日本民间叙事研究中,已经体现出后经典叙事学带来的冲击。五个新向度中最早出现的语用学转换,对民间叙事而言就是对叙事的意义和功能的强调。武田正在『「語り」の類型と機能』[p23-37](“叙事”的类型和机能)中,谈到了叙事范畴扩大的问题,并就新的叙事范畴内各种叙事的机能进行了初步探讨。高桥晋一的『「はなし」の社会的機能—阿波の狸話をめぐって—』[p210-240](“话语”的社会机能—以阿波的狸故事为例—)是一个典型的以一类故事为例,举证一类行为的功能的论述。铃木正崇的『湯立神楽の意味と機能ー遠山霜月祭の考察』[p247-269](汤立神乐的意味和机能—远山霜月祭的考察)则是对一类叙事活动在特定的语境中体现的意义进行考察。
意识形态介入叙事学,主要是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带来的影响,强调叙事的解释意义和政治解读。或许是日本民间叙事的研究者们讳言政治话题,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见。川浦佐知子对北方夏安族人的身份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可以作为代表。她在2006年到2009年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文,对北方夏安族人的自我叙事和集体记忆进行了详细考察,从他们的叙事中观察部族对自身的身份认知状况。
女性主义本身的历史比叙事学还要长,介入叙事学后,主要的影响还是在对叙事者特征的关注上,对其行为模式、文化程式进行含蓄的性别化。日本民间叙事研究者们很早就关注到女性问题,但主要是文本中的女性,例如对女神的探讨。对女性叙事者或者叙事者的性别问题进行考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间宫史子的『昔話研究と女性—ドイツ』[p139-145](故事研究与女性—德国),主要借鉴了德国在女性主义问题上的研究。藤井贞和的『聖伝にみる神話構造と叙述—アイヌ・女性・口承文芸』[p104-108](圣传中的神话结构和叙述—阿伊努·女性·口头文学)主要对少数民族阿伊努族女性口头文学的结构进行了解说,并强调了其作为女性文学的特征。荻原直子的『女性の語りの妙-カムイユカラ(神謡)の問題-』[p109-113](女性叙事者的妙—カムイユカラ(神谣)的问题—)则直接对女性叙事者的特质进行考察,在并非女性独占的神谣中发现女性叙事者的特征,这是之前的研究所没有的。
叙事向新媒介的渗透,意味着叙事的扩大化或者普泛化。近年来,我们确实看到日本学者的不少成果体现出这种倾向,例如纯丘曜章的『人気テレビ番組の文法』(人气电视节目的语法),森田均的『ハイパーテキスト文学論』[p327-334](超文本文学论),川本玲子的『物語論と「意識の科学」-自閉症の視点から』[p105-127](叙事学和“意识的科学”—从自闭症的视点来看)。这些成果基本来自其他诸如传媒学、计算机科学、医学等学科对叙事学理论的征用,但就民间叙事理论而言,向新媒介的渗透还不够,只有表演理论在教育学等领域有少量的成果,例如久次弘子的『パフォーマンス理論を授業に導入する試み:短期大学における:大学教育と演劇』[p109-125,174-175](表演理论导入授课的尝试:短期大学中的大学教育与演剧)等。
认知论转向是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股思潮,在叙事学中体现为认知叙事学。目前日本学者涉及这一理论的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西田谷洋的一系列研究:『認知物語論とは何か?』(何谓认知叙事学?),『認知物語論キーワード』(认知叙事学的关键词)以及『認知物語論の臨界領域』(认知叙事学的临界领域)。从这些研究来看,认知叙事学在日本还处于起步和学科界定阶段,目前尚未发现在民间叙事领域的运用。
从以上这些新的动向产生的成果来看,在整个日本民间叙事研究领域中还不很大,但成长势头较猛,冲击力很强。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结语
日本民间叙事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其中不乏使用西方新理论、新方法取得的成绩。纵观这些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首先,各阶段研究成果的出现,在时间上与西方并不完全一致。从研究对象来看,没有严格遵循从叙事到叙事者再到叙事活动的发展脉络。虽然起始的时间略有差异,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了。而且新的研究焦点的出现并没有取代之前的研究,即使到今天,对叙事文本的研究和叙事者的研究还不断有新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涌现,展现出民间叙事研究强大的生命力。从新出现的研究范式来看,后经典叙事学的五个向度在日本的发展也并不均衡。这一方面有理论产生先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日本学者的主动选择有关。
其次,日本学者的研究重视实证与应用,较少理论构建。无论是对叙事还是叙事者或者叙事活动的研究,他们往往是以某一个或一组具体叙事为对象,进行微观甚至精细的研究,叙事理论只是作为辅助手段来使用。他们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和运用,习惯用事实和例证来说明问题。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宏观的思辨的研究较少,在理论高度上有所欠缺。
此外,虽然在材料中并未充分体现,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日本民间叙事研究的学者们大多是跨界研究,几乎没有专门研究民间叙事理论的学者。目前的民间叙事研究者主要是来自文学和民俗学两大领域,也有少数医学、传媒、社会学、艺术等领域的学者参与。文学学者们对叙事理论较为熟悉,但大多数研究都在作家文学上,只是偶尔以民间叙事为对象;民俗学者们的研究对象虽然在民间,但总体而言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居多,较少使用现代叙事理论工具,从叙事角度进行研究。这使得日本民间叙事理论研究的地位有些尴尬,似乎夹在文学和民俗学两条并行的轨道中间,得不到充分的成长。
目前而言,叙事理论的中心仍然在欧美,我们对欧美叙事理论的借鉴仍是有必要的。日本民间叙事研究的学者们在使用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为理论的本土化进行了很大的努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理论工具选择的谨慎,并不是见了就拿,拿了就用。日本学者的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欢迎投稿
栏目主编的邮箱:
yunafk929@163.com
公号公共邮箱:
folklore_forum@126.com
(这个邮箱请注明新青年)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03期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中国民俗学会 · 业务范围
理论研究 学术交流 业务培训
书刊编辑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中国民俗学会
微信号 : ChinaFolkloreSociety
微信订阅号:民俗学论坛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民俗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