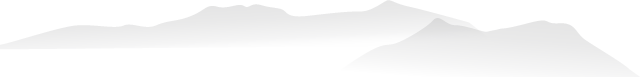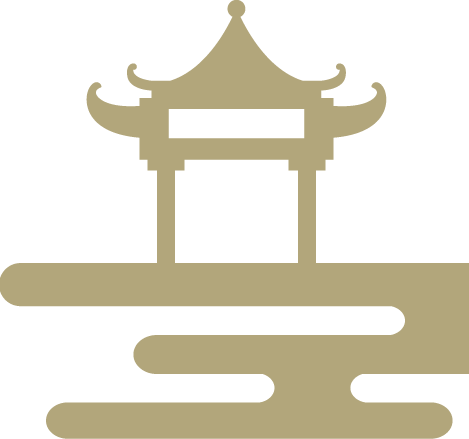本期新青年任志强,男,河南卫辉人,山东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中原非遗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传说、故事研究及中原民俗研究。伴随着电影《妖猫传》的上映,人们开始热议古代妖怪文化。其实唐代最著名的妖怪不是猫,而是狐。论文考察了精怪故事类型中的狐精故事,从狐与胡的关系入手,以中西文化交通的视角重新审视解读唐代狐精故事。
主编推介
狐与胡:唐代狐精故事中的文化他者
任志强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摘 要:在唐代,狐狸精故事十分兴盛,数量在精怪故事中位居首位。仔细阅读这些故事,可以发现故事中的狐狸精并非作者简单的精怪想象,而是对入居中土的西域胡人的隐喻。二者在体貌、服饰、发型、习俗、姓氏、文字、信仰、职业等诸多方面,存在彼此相通之处。这一现象与唐代中西交流、胡人大量来华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以狐喻胡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重新审视唐代的狐精故事,可以发现这些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入居中土后胡人作为文化他者在汉人社会中的生活遭际及其边缘身份,这或可作为中西交流的参考史料加以利用和研究。
关键词:狐精故事;西域胡人;中西交通;文化他者
唐张鷟《朝野佥载》云:“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在宋人编辑的主要以唐代作品为主的笔记小说集《太平广记》中,狐精故事就达九卷之多,在精怪一类中居首。这些均表明在有唐一代狐精故事和狐神信仰盛行的状况,然而关于狐的故事及信仰早已有之并不始于唐,为何却在唐代如此兴盛?唐代故事中的狐狸精怪仅仅是一种想象还是另有原型?
关于狐与胡的关系,学界已经作了一定的研究:陈寅恪先生最先指出狐臭与胡人之间的联系,认为腋气初为西域胡人的生理特征,因而“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应称为“胡臭”;等到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之后黄永年先生将此论进一步推进,指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西域胡人东迁日众,才使得“狐臭”与“胡臭”联系起来;“狐臭”之词逐渐取代“胡臭”而流行的关键,在于当时社会上有着“以‘狐’诟‘胡’”这种风气的普遍存在。这两位学界前辈的研究均从考证狐臭与胡臭两词的历史渊源入手,指出了狐与胡存在的关联,但并未能对此加以充分展开论述;当代学者王青在研究中探讨了中古时期狐怪故事与西域胡人及其文化的对应关系,但对狐与胡相通的证据分析不够充分,对狐精故事文本本身的研究也略嫌不足。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太平广记》中的狐精故事记载为主要资料来源,从中西交通的视野出发,全面梳理唐代狐狸精故事中狐与胡相通的各种证据,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背景,并透析唐代狐精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以利于人们重新理解这些故事的真正意涵。

1
唐代狐精故事中“以狐喻胡”现象举例
古代汉人习惯将华夏边缘的民族视为蛮夷,即近乎野兽边缘的人。不仅将这些部族的名字加上象征动物的部首,而且用动物的习性来形容他们的体貌特征和生活习性。在唐代,人们习惯将来自西域中亚一带印欧语系的人种视为胡人,其中尤以粟特人为最。在中古时期,狐与胡是两个同音异义的字,同韵、同调,同音反切。在唐代狐精故事中,狐与胡相通的现象随处可见。下面分别举例述之。
(一)狐臭与胡臭
根据陈寅恪的研究,中古时期的中国人称腋下散发出来的恶臭为“狐臭”,很可能就是源自“胡臭”,因为人们认为这种臭味一定是外来的,肯定是西来的胡人带入中国的。由于语音的关系,“狐”字经常被唐人用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异文化感觉,如同狐狸身上散发的恶臭。
狐与胡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六朝志怪小说《异苑》中,有个名叫胡道洽的人,“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
在唐代教坊司中,一位来自中亚的舞伎不仅像狐魅那样“有姿媚”,且体“微愠羝”,此即“狐臭”的委婉说法而已。住在蜀地的李珣是波斯人后裔,他文采斐然,“所吟诗句往往动人”,但却遭到文友以狐臭为由的嘲笑:“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
(二)“白衣”与胡服颜色
狐精故事中的化身无论男女以着白衣居多,如《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四“尹瑗”条(出《宣室志》)中的狐精是位“白衣丈夫”,卷第四百四十九“林景玄”条(出《宣室志》)中的老狐“衣素衣,髯白而长”,卷第四百五十“祁县民”条(出《宣室志》)中的狐精所化为“白衣妇人”,卷第四百五十四“韦氏子”条(出《宣室志》)中的狐精化身为“素衣”女子,沈既济《任氏传》中的任氏也是身着白衣。
穿白衣,是西域胡人的穿着习惯。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记载:“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指出西域服色禁忌:“吉乃素服,凶则皂衣。”此书多处记载了西域各国服白衣的习俗。
(三)“截发”与胡人发型
狐精故事中时有狐精截人发的记载。如《广记》卷第四百五十“靳守贞”条(出《纪闻》)云:
霍邑,古吕州也,城池甚固。县令宅东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厉王城,则《左传》所称:“万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远,则有狐魅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断其发,有如刀割。
狐魅截发在北朝时就有记载。《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孙岩的狐妻被孙岩发觉疑似狐魅后,临走时竟将孙岩发截掉,后京邑被截发者竟多达130余人。这种事在正史中也有记载,《魏书》卷一百一十二上《灵徵志》“毛虫之孽”条载:“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发”,“肃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师有狐魅截人发,人相惊恐”。《北齐书·后主纪》云武平四年正月:“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更早的记载出现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中写老狸精被除,“明旦发楼屋,得所髡人结百余”。《搜神记》记载此事时作老狐,“结”作“髻”,都是指人的发髻。狐魅截发或与头发含有人之精气、狐魅吸人精气有关,不过截发也透露出了狐魅与胡人存在关联的蛛丝马迹。
史书记载,截发是西域男性胡人之常见发式。《魏书·西域传·康国》载:“丈夫剪发,锦袍。”《大唐西域记》说象主之国,“断发长髭”,黑岭已来,“断发裂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载罽宾、犯引、吐火罗、波斯、大食以及安、曹、史、石骡、米、康诸国,“此等胡国,并剪鬓发”。狐魅故事中记载的“截发”现象反映了西域发式开始流入中土时所引起的惊异之感。
(四)“畏狗”与胡人葬俗
在狐精故事中,狐如果以男性形象示人,最常见的形象通常是一老者,并通常具有畏狗的特征。《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习凿齿”条(出《渚宫故事》)云:“晋习凿齿为桓温主簿,从温出猎。时大雪,于临江城西,见草雪上气出。觉有物,射之,应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带绛缯香囊。”男性狐怪多老者形象,显然与西域胡人多须髯、面相苍老有关。至于佩带香囊表明当时许多西域贾胡从事香料买卖有关。胡人之畏狗,则与他们的葬俗有关。
以康国为例,唐杜佑《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边防·康居》引韦节《西番记》曰:“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可见康国等西域国家流行弃尸饲狗、收骨埋殡之俗。《旧唐书》卷第一百一十二《李暠传》:“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岑仲勉先生认为:“此实袄教之习俗,所谓黄坑,西人称曰无言台。”祆教是古代流行于波斯及中亚等地的宗教,中国史称祆教或拜火教。蔡鸿生先生认为此乃天竺古法,为印度式野葬。所以,见狗即被视为不祥,这或许是狐精畏狗这一特征的文化来源。
(五)狐精姓氏与胡人改姓
在狐精故事中,狐精采用的姓氏也反映出其出自胡人的线索。狐精多采用胡作为姓氏,当然也有采用其他姓氏的。如 《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唐参军”条(出《广异记》)中有个狐男这样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之狐,姓白姓康。”
胡人改姓汉姓,也是他们逐渐汉化的过程。唐朝时期,成千上万的胡人涌入唐帝国,和汉家女子成婚,定居中国改汉姓。来自康居者以康为氏,安国者以安为氏,月支者以支为氏,曹国者以曹为氏,鄯善者以鄯为氏,这是以原所在国为姓氏者。此外,龟兹人姓白,焉耆人姓龙,疏勒人姓裴,于阗人姓尉迟。西域胡人始入中华虽用汉姓,但其名字往往仍留西域痕迹,至下一代则姓名始俱华化。如裴沙字钵罗,中唐时入唐,嗣子名祥;裴玢五世祖名纠,至玢当已华化,故名为玢。安朏汉以贞观时入唐,子附国当属赐名,附国子思祇、思恭;安波主子恩顺,则姓名俱华化矣。
“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之狐,姓白姓康。”这一俗语暗示“千年之狐”(来华已久的胡人)已具有纯中国化的姓氏,而“五百年之狐”(来华不不久的胡人)的姓氏则仍带有胡人的气息,狐狸人格化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胡人汉化的程度。
(六)“狐书”与胡人文字
在狐精故事中,狐所读之书往往为汉人所不识之文字或不懂之经籍。《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四“张简栖”条写南阳人张简栖在墓穴中发现有个狐狸在看书,他从洞穴中偷得一书,书的装订方式、纸张、用墨都与人间书籍无异,但文字“皆狐书,不可识”。《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三“王生”条(出《灵怪录》)记录了杭州王生捡得野狐所遗之书,同样是“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九“林景玄”条(出《宣室志》)讲到,京兆人林景玄打猎途中在墓穴看到一个老头穿着白衣服,胡子白且长,手里拿着一轴书。林景玄把墓穴毁了,老头变成一只老狐狸,林就把狐狸射死了。看看那轴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白绢做成,长仅数十尺。这类“似梵书而非梵字”,汉人不识之文字,很可能就是是粟特文之类的波斯系统文字。
又如《玄怪录》“狐诵通天经”条:“裴仲元家鄠北,因逐兔入大冢,有狐凭棺读书。仲元搏之不中,取书以归,字不可认识。忽有胡秀才请见,曰行周,乃凭棺读书者。裴曰:‘何书也?’曰:‘《通天经》,非人间所习。足下诚无所用,愿奉百金赎之。’”汉人不可认识之《通天经》,疑是袄教、摩尼教之类的西域宗教经籍。
类似例子尚有《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一“孙甑生”条(出《广异记》),其曰:“唐道士孙甑生……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甑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甑生不与。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甑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老狐所传之书为唐人孙甑生所不解,应该也是以西域文字书写的经籍。
许多故事中提到狐所读的天书文字似梵文,且多为人所不识,这与当时大量西域佛经传入中土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
(七)狐精形象与佛教
唐代佛教的盛行,强化了狐狸与胡人之间的关系。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印度密宗大师先后来到中国弘扬密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三大士”。
密教以咒术、占卜、医药为主要手段,在翻译的密宗文献中,经常出现“狐魅”的字眼,这些文献将狐魅、山魈和恶鬼并列,认为这些是致病的主因。在密教中,狐魅指的是一个被大日如来佛制服的恶魔狮空行母(吒枳尼真天)。在日本,吒枳尼真天被描绘成一个骑在白狐身上的女神。
相较于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佛教教派,密教因与外族僧人关系密切,故胡人意味更浓一些。玄宗经常鼓励印度密教法师与中国道士当庭竞技,由此凸显道教的中土之源与密教的异域之根,强化胡人与这个佛教教派的关联。
在唐代与佛道有关的故事中,狐精还常以佛陀、菩萨或胡僧的面貌出现,暗示出胡僧和狐精的身份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互换。在《广记》卷第四百四十八“叶法善”条(出《纪闻》)记载,一个出身名族的人其家中女眷二十余人被一婆罗门僧人引导着进入催眠状态,她们虔诚地跟随在胡僧之后,齐声念佛,进行佛教仪式。此人遂赶忙求助当时的著名道士叶法善,叶法善称该婆罗门僧乃天狐,“能与天通,斥之则已,杀之不可”,于是送给他一道符。他用那道符唤醒女眷,并将胡僧捆绑起来交给叶法善。惧怕于法师高强的法力,胡僧弃袈裟于地,现出狐狸原形。鞭打数百下后,法善将袈裟还给他,遂恢复婆罗门僧形貌,被放逐千里之外。
唐代佛道斗法的历史背景让我们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唐代的道士希望像叶法善使胡僧现出原形被逐出境一样,能比胡僧高人一等,并将他们赶出自己的土地。在另一则狐精故事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九“韦明府”条(出《广异记》)中,强逼凡女成婚的狐精最后被驱逐到“长流沙碛”,指的正是黄沙瀚海的中亚。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大安和尚”条(出《广异记》)记载了武则天在位时期中土和尚挑战圣菩萨的事件,最后圣菩萨“词屈,变作牝狐,下阶而走,不知所适”。武则天在位时期,宣称自己是弥勒降生,将自己塑造成类似故事中“圣菩萨”的形象。但武后夺权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挑战,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斥其“狐媚偏能惑主”,这则故事反映出当时的一些士大夫将武则天视为挑战儒家传统男性权威的外来者,类似闯进中土的胡僧一般,令人想逐之而后快。
狐何以化成佛和菩萨呢?首先应归于人们对其虔诚之信仰。如《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一“长孙甲”条(出《广异记》)说:“(长孙甲)家笃信佛道,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合家礼敬恳至……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又如上引“叶法善”条说:“妇人见一婆罗门僧,皆下车从之,齐声称佛。佛执花前后,妇人随后作法事,如至天堂,其乐不可言。”人们对佛教的笃信,使佛、菩萨在民间得到崇信,这是狐化佛、菩萨的前提。另一方面佛教产生于印度,流传于西域各国,胡人多信仰佛教,故作为胡人隐喻之狐亦偏爱佛教,化身佛或菩萨以宣扬佛法。
(八)狐精职业与胡人
阅读唐代狐精故事,可以发现狐精的职业与胡人也有关系。
狐女多擅长音乐歌舞,如《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一“僧晏通”条(出《集异记》)说狐化成女人后自称为歌人。卷第四百五十二“任氏”条(出《任氏传》)说任氏为狐,其兄弟名系教坊,其内姊女为刁将军家之善吹笙者。从西域而来的胡女在中土多以歌舞为生,唐代的乐工也多为胡人或胡裔。《唐会要》卷三十三和卷三十四中记载的乐人就有舞人安奴、乐工白明达,善觱栗的尉迟青,善吹笙的尉迟章,琵琶第一手康昆仑,还有琵琶手曹家三世。所以说胡人在唐代是以音乐歌舞著称的,这和狐魅所变女子多以歌舞见长,绝非巧合。
狐女善媚的形象特征,除了古人有狐性淫的认识以外,也与胡女所从事的职业不无关系。西域之色情业较之中土发达。《魏书·西域传》载:“(龟兹)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新唐书·西域传》亦载:“葱岭以东俗喜淫,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西域商胡一直从事女奴买卖,此类妇女入居中土亦不足为奇。就其以歌舞侍酒为生来看,其为娼为妾也是十分常见的。如《广记》卷第四百五十“薛迥”条(出《广异记》)说,薛迥于东都狎娼妇,一夕午夜,娼化狐而去。而卷第四百五十二“任氏”条(出《任氏传》中任氏自己介绍说:“生长秦城,家本伶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以是长安狭斜,悉与之通。”
狐女还有经商的特长,这与胡人善于经商的特点完全契合。如任氏不习汉族妇女都会的女红,却对商贾攫利之事颇为擅长,任氏之表娣妹张十五娘也善做生意,她是鄽中鬻衣之妇。
狐男的形象也值得一提, 狐化为男子最喜魅惑诱骗美女。如《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长孙无忌”条(出《广异记》)说:长孙无忌的一美妃被天狐迷惑,每见无忌,便持长刀斫刺。又卷第四百四十八“杨伯成”条(出《广异记》)说:吴南鹤(狐)看中了杨伯成之女,因无媒而自荐,遭到拒绝后,大怒,呼伯成为老奴,慢辞甚众。久之,女为狐媚。有更甚者,狐男竟好偷美妇,如卷第四百四十八“刘甲”条(出《广异记》)讲,刘甲之妻美,为狐所窃,后发现一古冢丈余,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这些狐男贪婪如此,正如现实中擅长经商、财大气粗的商胡所为。胡人以善经商为名,多豪商大贾。他们从中原购买丝绸,从西域运来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频繁往来于丝绸之路上。
一些胡商还从事着贩卖人口的勾当,他们从西域贩运许多胡女来华充当歌妓、舞女等,但也以非法手段抢掠或拐卖中原妇女。《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代宗大历十四年“庚辰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不仅如此,胡人还掠夺中原妇女带回本国,《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张光晟传》就记载了一起胡人拐卖汉女的案件:“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槖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由此可以推测当时被掠走的妇女为数肯定不少。肃代之际,回纥取代了突厥,在中原肆无忌惮,《唐会要》卷一百“杂录”记载,“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但回纥等诸胡仍不受约束。可见狐精故事中所反映的胡人“诱婚”问题确实存在。
此外,古代婚姻中存在卖婚的现象,这在唐代狐精故事中也有所体现。如《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一“李黁”条(出《广异记》)云: 李黁一故人以卖胡饼为业,其妇(狐)美,李黁以十五千索胡妇,宠遇甚至。又如卷第四百五十五“昝规”条(出《奇事记》)说: 昝规儿女六人尽孩幼,然贫乏委地,存活无路,以十万卖妻于老父(狐)。又卷第四百四十九“韦明府”条(出《广异记》)说:韦明府答应将女儿嫁给崔氏(狐),条件是以二千贯为聘,多以钱为婚。因胡人多为商贾,财大气粗、甚是有钱,故时人以利卖婚于胡人,当为事实。

2
狐胡相通的中西交通背景
南北朝以来,尤其是隋唐之世,大量胡人涌入中原,致使唐代社会生活胡化现象十分突出。《大唐新语》卷十记载:“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幂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显庆中,诏曰:‘百家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罗;曾不乘车,只坐檐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神龙之末,幂罗始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就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安史之乱后,胡人大量地进入内地,《东城老父传》发此感慨:“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这是当时人眼中的长安城。两都为胡化最为严重者,唐代元稹的《法曲》对此有十分形象的描写:“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胡人进入中原,时间一久便定居下来不再想回去。《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二记载说:“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朝野佥载》卷五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盖宋氏乃入居中国之久者。
胡人来华日久,人们对胡人便不再陌生。《朝野佥载》卷六记载:“后赵石勒将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险鸩毒,有儿啼,母辄恐之‘麻胡来’,啼声绝,至今以为故事。”胡人深入民间,童叟皆知。即使在汉人所谓的阴曹地府中,也可见到胡人的踪迹,《广异记》“阿六”条写饶州一奴名阿六,死后,欲还人世,遇到了以前一个相识的胡人,他求阿六捎书回家,以诉他在阴间所受的煎熬。这说明人们已经接受了与胡人杂居的现实。
胡人来到唐帝国,带来了与汉文化迥然有别的异文化,对此唐人有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对胡人带来的异域物质和精神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方面又对胡人存有疑虑、担忧、歧视乃至不屑。在唐朝任职的两个著名的非汉人将领安禄山和哥舒翰之间的对话,暴露了当时社会上以狐喻胡的风气,并显示出“狐”是对胡人藐视性的一个称呼。
翰素与禄山、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其冬,禄山、思顺、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旧唐书》卷九十《杨再思传》记载了一个类似的事情,说杨再思为人巧佞邪媚,为人所恶,其面似高丽,故戴令言作《两脚野狐赋》以讥刺之,再思闻之甚怒。这正同安禄山一闻“野狐”便大怒,说明唐人以“野狐”来讥诮胡人已非常流行。以狐指称胡人其实并不始于唐代,其实早在在晋时,狐为胡之象征就已存在。《太平御览》卷第九百九《兽部二十一》引《晋书》曰: “凉武昭王暠子歆,为凉州牧。时有狐上南门,主簿汜称曰:‘谚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狐上南门,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有胡人居於此城,南面而君也。’后竟为沮渠蒙逊所灭。”
胡人进入内地愈多,胡与狐联系就越紧密,从而导致唐代出现大量关于狐的故事。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主要是对隋唐前小说的辑佚,其中讲狐的只有三条,而以唐人小说为主的《太平广记》中狐精故事竟达九卷,在精怪故事中居首,足见唐代狐故事之丰富。唐张鷟《朝野佥载》记载:“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狐神信仰流行之广,可见一斑。古人以为狐真会化为人作怪,《广记》卷第四百五十“田氏子”条(出《纪闻》)还讲了一件因误认对方是狐魅引出的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说两人同过栎林,彼此怀疑对方是狐魅,在互相殴打中,两败俱伤。有一则更可笑,《广记》卷第二百八十八“纥干狐尾”条(出《广古今五行记》)说,并州有人姓纥干的人喜欢开玩笑,一天他得到一条狐狸尾巴,随即就拴在了衣服后面。来到妻子身旁,他侧身而坐,故意将狐狸尾巴露在外边。妻子见了,暗自怀疑他是狐狸精,于是便悄悄操起斧头向他砍来。他吓得连忙磕头说:“我不是狐狸精!”这些记载表明表明关于狐魅的传闻及信仰在当时的社会中已非常普及。

3
唐代狐精故事:作为文化他者的胡人生活遭际的反映
如果胡狐相通成立的话,那么唐代狐精故事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胡人来华生活的遭际,这或可视作中西文化交流的参考史料加以利用,必将有助于中西交通史的深入研究。
盛唐时期,西域胡人大量涌入长安,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达到顶峰,对唐人而言,西方的印度和中亚,是普渡众生的佛教发源地,也是拥有奇珍异宝和奇玄幻术之地。西胡的涌入,带来了不同于汉人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同时也危险到汉人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产生对外族和外来势力的敌意并逐渐加深。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大衰,此时对外来事物的感受更为敏感。在时人的观念中,汉人与胡人有着一种文化上内外之别,空间上的内外之别,胡人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文化他者。唐代狐精故事,在一定程度是反映了胡人来华后的生活遭际和边缘身份。
从唐朝开始,故事中狐精之命运较唐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上表中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狐精的最后结局或被杀,或被重罚,或被驱赶,表明胡人来华后的遭遇并不乐观,甚至相当悲惨。结合唐代狐精故事,我们会对这种情况有更加真切的体会。
《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九“谢混之”条(出《广异记)载谢混之为东光县时,“以严酷强暴为政,河南著称。混之尝大猎于县东,杀狐狼甚众”。其后有一人告谢混之杀其父兄。中书令张九龄令御史张晓去追查此事,并和讼者同往。“晓素与混之相善,先蹑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其后将混之入于狱中。“有里正从寺门前过,门外金刚有木室扁护甚固。闻金刚下有人语声。其肩以锁,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听之。闻其祝云:‘县令无状,杀我父兄。今我二弟诣台诉冤,使人将至,愿大神庇荫,令得理。’”在公堂上,“讼者言词忿争,理无所屈”,“有识者劝令求猎犬,猎犬至,见讼者,直前搏逐。径跳上屋,化为一狐而去”。父兄被杀而诉讼无门,可谓悲惨至极。胡人由于遭受歧视,在社会上往往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官府对这一现象也往往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与汉人的通婚中,胡人同样会遭受歧视、不解乃至被抛弃的命运。《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一“李黁”条(出《广异记》)说,李黁得官自东京赴任时,夜投于故城,见有胡妻貌甚美,便以十五千钱以索之,到东平后,甚是宠爱。其妻“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至故城后,其妻言腹痛,后下马,飞奔于小穴之中,呼之而无所应。第一天即用火燻亦不应,后村人挖掘得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蜕,乃其妻也。归店后即用猎犬噬其子,而子不怕,寄其子于亲人家中养育,而李黁也被称之为“野狐婿”。其子寄人篱下,且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可谓是屡受虐待。一场胡汉婚姻,最终却落得妻死子散的悲惨结局。这则故事也说明,胡汉婚姻在当时不为社会所接受,所生的孤儿也寄人篱下倍受歧视。
《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一“贺兰进明”条(出《广异记》)载:贺兰进明为狐所婚,其妇貌甚美,每至五月五日,便为家人送来礼物,家人以为不祥,便多焚之。“狐悲泣云:‘此并真物,奈何焚之?’”,后因其家人有求漆背金花镜者,便入人家去偷,以尝家人心愿,孰料却被人发现后所击杀,结尾却说“自尔怪绝焉”,家人可谓对她毫无感激之情或亲情可言,甚至连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同卷“王璿”条(出《广异记》)记载,宋州刺史王璿“为牝狐所媚”。狐精“自称新妇,祗对皆有理”,大家都很喜欢她,她每逢节日也都有礼品赠送给家人,然而结局却是“后璿职高,狐乃不至”。这两则故事都表明胡女试图融入汉人家庭所遭遇的那种尴尬窘境。为了博取男方家庭的认可,必将赠送大量礼品,在家庭中谨小慎微,毕恭毕敬,可见其在家庭中地位的卑微,然而两个狐精最终的结局更令人唏嘘不已:一个是因男方家人贪得无厌死于非命,一个是在男方官高位尊后被迫离开。

4
结语
唐代中西交流频繁,胡人大量来华。在唐人眼中,狐与胡是相通的,二者在体貌、服饰、发型、习俗、姓氏、文字、信仰、职业等诸多方面,存在彼此相通之处。唐人把对胡人的敌意和偏见加之于狐身上,不仅导致狐精故事的大量产生,也导致狐精故事中狐悲剧命运屡屡出现。可以说,狐精故事正反映了胡人来华后的生活遭际。随着胡汉民族的交融日益密切,来华的胡人进一步汉化,胡汉之间的隔阂逐渐缩小,反映在小说故事中的民族歧视和偏见也逐渐减少,唐以后狐精故事中嘲讽影射异族的色彩就明显淡化了。
笔记小说作为历史记录的有效性,在汉学界尤其是海外汉学界已广为研究中国历史和宗教的学者接受。康儒博(Robert Conpany)对向来认为志怪小说不过是虚构作品的观念提出质疑,他在中国中古早期志怪小说研究里证明志怪小说是被编辑用来使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议题臻于完整、可证实的历史记述。韩明士(Robert Hymes)通过对《夷坚志》的研究,主张笔记和志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史学,让文人用以讨论神祇、鬼怪和其他五花八门、不登正式文类的主题。美籍华裔学者康笑菲也认为,传统笔记和志怪文类里确实有其真实性,许多明清时代狐精故事的编纂者采取类似编写正史时所用的严谨态度和格式。他们向各种各样的人搜集故事,力求正确无误的誊写那些故事,主张忠于真相的精神。基于此,笔者认为,记载狐精故事的这些志怪小说尽管一些情节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变形,但作者大多遵循的是实录记史的写作态度,尤其是故事表现出的历史情境以及反映出的当时人的观念心态是真实的,它们从整体上和宏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真实和历史真实。因此,我们可以说,唐代狐精故事是特定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文化他者的胡人入居中土后的生活遭遇及其边缘身份,这或可视作中西文化交流的参考史料加以研究和探析。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栏目主编的邮箱:yunafk929@163.com
公号公共邮箱:folklore_forum@126.com(这个邮箱请注明新青年)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新
●
青
●
年
专栏连载
拓展阅读
34.新青年 | 李文钢: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以宁边村四个族群为中心讨论
33.新青年 | 游红霞:民族节日的公共化——上海的满族颁金节
32.新青年 | 李华:散杂居地区回民婚俗文化探析——以山东地方镇为例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中国民俗学会 · 业务范围
理论研究 学术交流 业务培训
书刊编辑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中国民俗学会
微信号 : ChinaFolkloreSociety
微信订阅号:民俗学论坛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民俗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