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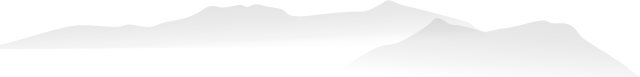
本期新青年马千里,男,安徽六安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民俗学专业博士生。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国民俗学史。他的这篇文章涉及了中国民俗学关注较少的一个领域。他站在国际法语地区的宏观视野中,以凯尔特学会为中心,梳理了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民俗学运动。
主编推介
法国民俗学的史前史
——凯尔特学会钩沉(1804 – 1813)
法国民俗学学科通史是中外学界较少涉及的一个领域。事实上在法国国内,由于历史上某些政治和学科理念的因素,作为学科名称的“民俗学”(folklore)在二战后已逐渐被“法国民族学”(ethnologie française)所取代,对该领域学术史的研究也并非热点。尽管如此,法国民俗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兴起、发展、困顿与坚持是欧洲民俗学学科史的有机构成,至少对早期的德国民俗学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民俗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一般认为,现代法国民俗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1804—1815)凯尔特学会(Académie celtique)的民俗调查活动。以下通过探寻凯尔特学会成立的思想和政治背景,勾勒学会的主要活动并着重介绍其民间传统调查问卷,进而探讨学会活动的学术意义及其对早期法国和德国民俗学的影响。
一、凯尔特学会的若干源头
与德国、芬兰等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俗学相似,法国民俗学源于18世纪中叶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直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本民族文化古希腊罗马起源观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开始受到强烈挑战,法国和英国开始将古凯尔特文化视为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内核与民族文化源头,将其与古希腊罗马起源观相抗衡。在法国,民族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龙沙(Ronsard)创作的史诗《法兰西亚德》(La Franciade)。这部作品有着明显模仿古罗马文人史诗《埃涅阿斯记》(Aeneis)的痕迹,描绘了主人公赫克托耳(Hector)之子弗朗库斯(Francus)这一虚构人物历经艰险开创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故事。尽管《法兰西亚德》并未达到龙沙代表作的水平,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相当有限,但它作为一部以写实笔法创作虚构情节的文人史诗,响应了法国文艺复兴期间构建法兰西民族认同的需要,并且作为第一部用法语创作的文人民族史诗被当时七星诗社(La Pléiade)的另一位代表性诗人杜贝莱(Du Bellay)认为是一部“使得法语高昂头颅”之作。1760年,莪相(Ossian,三世纪苏格兰诗人,被称为凯尔特人的维吉尔)的诗作被翻译成英语,为当时的文化和政治领袖提供了有别于欧洲古希腊罗马起源观的诗性观点。而作为拿破仑喜爱的诗人,莪相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被用来制造法兰西民族文化的凯尔特文明起源论这一新的文明观。
另一方面,法兰西第一帝国为了加强国家权力,构造“学术国家”(Etat scientifique)的形象,巩固大革命的成果,开始构思建立一个大范围的政治和组织机制,使得学术活动也积极参与到国家层面的规划中去。而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来证明法兰西民族文化的凯尔特文明起源论,以打破法兰西民族文化的古希腊罗马起源观则成为法国民俗研究机构的雏形——凯尔特学会的主要政治目的。(Jean-François,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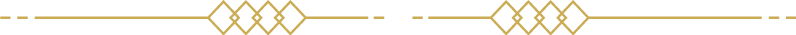
凯尔特学会的活动宗旨在其常设秘书埃洛瓦·若阿诺(Eloi Johanneau)在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有着明确的体现:
学会提出的双重目的既是重要的,又是有用和明确的;这就是对凯尔特语言和古物的研究……因此我们的目的应当是,首先从古代文献和古代遗存中来恢复凯尔特语;现存的凯尔特方言有两种,即布列塔尼语和威尔士语。此外所有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的民间方言、土语和隐语,以及从上述语言衍生出来的语言、神名、记忆和习俗的初始形式都需要恢复,需要在这些语言形式彻底消亡前抓紧时间对其进行登记造册,并为其编写词典和语法。第二,对所有的古物、记忆、习俗和传统进行采集、记录、比较和解释;一句话,就是对古代高卢进行数据统计并用现代来解释古代。
事实上,学会的会员们认为只要重建凯尔特语言和文化就有可能解释法国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方言,也能解释存留下来的令人不解的奇异建筑和看上去不再变化的信俗,例如农村里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风俗。这种文化退化观成为凯尔特学会的基本学术理念。而作为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俗研究的学科化建设的尝试,凯尔特学会的活动与语文学直接相关。当时的一些学者如拉图尔·都外涅-科雷(La Tour d’Auvergne-Corret)就在凯尔特诸语言是印欧语祖先的预设前提下去试图找到所有欧洲现代语言的凯尔特词源。

法兰西第一帝国对学会所主张的凯尔特文明起源观的支持可以从学会的研究对象及其解释中找到答案,即“在法兰西帝国境内曾经有过或者依然存在的实践活动。而法兰西帝国通过一系列伟大的军事胜利恢复并超过了古代高卢的势力范围。”在这里,研究的地域被限定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疆域,并且隐含着以古代高卢的凯尔特人以内核来构建当代法兰西民族国家认同的倾向。其实早在18世纪,布兰维利耶(Boulainvilliers)就提出,当时的贵族作为特权等级(l’ordre privilégié)是古代法兰克人的后代;而从大革命的视角来看,法兰西民族是由被法兰克人征服的民族即凯尔特人的后代构成的。这一观点成为凯尔特文明起源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并在19世纪被普遍接受。在上述排他性的民族观和对抗性的阶级观的影响下,作为法国民俗学前身的凯尔特语言文化研究已经参与到新时代精神下的法兰西民族定义的进程之中。
凯尔特学会的成立除了与其政治和民族理念直接相关外,也与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档案编制的理念有关。档案编制的理念在大革命期间由执政府(1799—1804)落实,并在第一帝国期间推广到全国,以在全国范围内分省建立统计数据档案。但编制这些档案基本上只是为了统治者了解法国的乡村地区,包括乡村的习俗和方言,以便改进国家治理的方式,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对本国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还是从凯尔特学会开始。
二、凯尔特学会的主要活动
凯尔特学会由三位凯尔特语言文化方面的博学之士在1804年创建。这三名创始人分别是植物学家、语文学家埃洛瓦·若阿诺(Eloi Johanneau, 1770-1851),地方行政官员、作家雅克·康布利(Jacques Cambry, 1749-1807)和外交官、革命派期刊《民族的埃罗省》(Le Héraut de la nation)的创刊者米开朗基罗-博纳赫·芒古里(Michel-Ange-Bernard Mangourit, 1752-1829)。1805年2月,学会在卢浮宫选举康布利为会长,若阿诺为常设秘书,芒古里为临时秘书,从而正式确定了学会的领导机构。学会正式的成立大会则在共和历8年芽月9日,即1805年3月30日召开。1807年,康布利去世,由法国古建筑博物馆的创始人和主要管理者亚历山大·勒努瓦(Alexandre Lenoir, 1761-1839)接任会长一职。
这一时期的法国基本还处在古物研究的阶段,尚未关注民俗事象的调查与采集,因而凯尔特学会的成立对于民俗调查和研究而言具有开拓意义。正如上文引用的埃洛瓦的发言,学会不仅要对“所有的古物、记忆、习俗和传统进行采集和记录”,同时也要对其进行“比较和解释”,而比较和解释的目的在于重建和恢复古代凯尔特人的高卢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凯尔特学会的基本学术理念与几个欧洲国家早期民俗学的立场大致一致,都体现出“遗留物”为内核的退化主义观点。学会文件中常见的”monumens”一词的词义就与其拉丁语词源”Monumentum”相一致,就是不仅包括建筑或建筑遗址,还涵盖信仰、习俗、传统和语言,即一切能够证明“祖先的荣耀”(Gloriae Maiorum)的物质与非物质形式的残留。“祖先的荣耀”也正是学会徽章上的铭言。
为了重构古代凯尔特人的高卢文明,学会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来编制一份调查问卷,调查当时存留在法国境内的民间习俗、信仰、建筑和语言。工作组由五人组成,拥有历史学、文学、语文学、工程学、地理学、绘图学、植物学等多学科背景。调查问卷包括51个问题,主要由芒古里和雅克·安托万·杜洛赫(Jacques Antoine Dulaure,1731-1813)设计,但将这些问题按顺序进行排列、分类和编写是由杜罗赫一人完成的。调查问卷完成于1805年7月,从1807年开始向每个省“最为见多识广的人士”发放,并由这些人将自己的答复寄给学会的常设秘书。收到的答复将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然后发表在学会的年鉴上。从共时的角度看,编写这份详细的调查问卷成为学会的基本学术活动之一;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该调查问卷成为凯尔特学会对后来的法国民俗学最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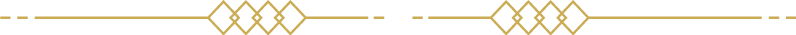
事实上,凯尔特学会编制调查问卷是为了回应第一帝国内政部长吕西安·波拿巴(Lucien Bonaparte)的指令。指令要求对大革命以来法国城乡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行记录。卢西安的继任者科代(Cretet)一方面领导相关部门(凯尔特学会)继续搜集所有乡村的代表性风俗,一方面通过翻译寓言来记录所有法国的方言(如布列塔尼语)。
调查问卷的51个问题共分为四大类,分别涉及不同的调查领域,每个大类都有明确的标题,分别为:
1. 岁时节日(如春秋分、夏至冬至、圣诞、元旦、五月节,圣人日和收获节等);
2. 人生礼仪和习俗(如诞生、成人、绝育、死亡和葬礼等);
3. 古建筑、古迹和现存的古风遗俗(如墓葬和有关信仰);
4. 其他信仰和遗存(superstitions)(如游戏、歌曲、舞蹈、乐器、童话、巫术、民间星相术、谜语和习俗等)。
这四个大类中每一类又分为若干个大问题,每个大问题又包括少则一个,多则十余个小的具体问题。例如第一大类岁时节日中的第14个大问题是关于收割节庆的,包括两个小问题,即收割时节结束时有什么节日与实践以及在收割大麦时怎样庆祝。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类中的“superstitions”表示的并不是该词的今义“迷信”,而是其词源的词义,即“已消亡的事物中遗存下来的部分”,也就是民俗学中“遗留物”的意思。这种退化论的民俗观在问卷的问题中也时有体现,如属于第一类的第15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小问题,即“(葡萄采摘时节结束的时候)是否有榨葡萄节和酒神节的遗存?”又如属于第四类的第28个问题中的第3个小问题,即“(当地)有没有一些听上去源自遥远古代的歌谣?”
作为见证了当时法国学术界民俗认识水平的珍贵文件,这份调查问卷发表在学会1807年度年鉴的第一卷上。年鉴在学会会员的集会上被分发和讨论。尽管学会的活动建立在信息提供者基层网络运行的基础上,但正如学会的一份建议书中规定的那样,学会也通过 “询问有关的人物、地点、事物和词语等”来进行直接调查。
在后来的法国民俗学家亨利·盖道兹(Henri Gaidoz, 1842-1932)看来,这份调查问卷“近乎是一份民俗学论文,标志着法国民族志的创建”。“过渡礼仪”(Rites de passage)理论的提倡者阿尔诺·范·热耐(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则认为,“这份调查问卷确实构建了一个如此杰出的框架,以至于至今它还有使用的价值,只要在物质生活、房屋类型和民间艺术方面添加若干问题即可。至于(问卷提出的)与仪式和我们所称的传统有关的问题,真的是无可指摘。”
随着1814年兵败滑铁卢后拿破仑的失势,学会也失去了国家的支持。早在帝国解体之前的1811年,学会就已面临危机,已经有人批评学会的工作,例如词源学的研究有夸大和带有偏见之嫌,同时那些热心的凯尔特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们自己也远离了民间传统。最关键的是,由于在词源解释上出现了过度阐释,有的解释也缺乏历史证据,学会没能说服公众接受现有的遗存起源于凯尔特文明这一观点。总之,由于研究的理论基础中主观的成分过多,同时又由于波旁王朝复辟所造成的政治风向转变,凯尔特学会没有完成构建法兰西民族国家认同的目的。1812年,学会出版了最后一卷,也是第六卷的年鉴,此后学会逐渐停止了活动。
1814年,原凯尔特学会的会员组建了法国古物学会(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古物学会主要研究语言、地理、年表、历史和凯尔特、希腊和罗马文学与文物,以及中世纪文学与文物,重点研究的是高卢人和16世纪以来的法兰西民族。作为凯尔特学会的继承者,法国古物学会除了研究凯尔特遗存物之外,还研究希腊和罗马文物,并延续了中世纪研究,而名为研究“现代遗留物”,实为对法国民俗资料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的搜集和研究则几乎完全被放弃了。1827年,学会的常设秘书长辞职,此后直到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即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路易·波拿巴执政期间才有调查民间诗歌的调查问卷被发放。
三、凯尔特学会活动的学术意义和影响
尽管存在着过度阐释的现象,凯尔特学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会摒弃了仅仅出于猎奇目的的民俗研究理念,在法国开启了系统化的民族志研究,突出了用于研究民俗事象的方法论的建构。作为学会的主要学术成果之一,民间传统调查问卷以其内容的全面性不仅得到后来的民俗学者的赞誉,为半个世纪后真正成型的法国民俗学打下基本研究框架,还在一个世纪以后被范·热耐在其著作《当代法国民俗学教程》(Manuel de folklore français contemporain)中引用。范·热耐将其视为第一个建立在形式和细节(形态学)基础上的调查表,他本人和保罗·塞比奥(Paul Sébillot)后来都运用过。范·热耐特别借用了其中的时令概念和主要的人生仪礼概念,但他拓展了研究的视域,探寻民间传统创造和传承所特有的心理动机和组织逻辑,以寻求民间传统的动因和功能。
除了塞比奥以外,凯尔特学会对其他以描述民俗事象为主要方法的民俗学者如Luzel和Rolland的民俗搜集工作都有所启发。后来研究仪式和功能的学者如皮埃尔·山狄夫(Pierre Saintyves)和范·热耐的研究理念也可以追溯到该学会。这一派关注的领域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遗留物”转变为有象征意义的活态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凯尔特学会的学术影响并不限于法国,学会还通过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对德国语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雅各布·格林曾经到巴黎学习中世纪文学和诗歌,同时利用这一机会搜集有关古代日耳曼人的习俗、法律和文学的资料。他在接触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以前的凯尔特人、罗曼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文学的材料时,通过日耳曼语言和神话接触并开始研究凯尔特文化。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一研究将其带入凯尔特学会,并因此对其未来的学术转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雅各布·格林于1811年成为学会的外籍通讯会员,并产生了在德国建立一个类似学会的想法。当然这一设想没能实现。但正是在凯尔特学会一定程度的影响下,格林兄弟开始试图找到塑造所有日耳曼民族语言的原始词源。在他们看来,这些原始词源通过日耳曼民族的法律和习俗体现出来。众所周知的是,格林兄弟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重视带有增强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目的,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到了法国凯尔特学会的启发。正是从以上的学术和政治理念出发,格林兄弟在德国最终开辟出了语文学(philologie)这门汇聚了比较语法学、语言学、文学史、神话学和传说学的综合学科。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水平已经超过法国的德国语文学又通过在德国留学的法国青年学者反过来从根本上促成了法国语文学派的民俗学的形成。
余论
作为开启法国民俗调查研究的学术组织,凯尔特学会的成立一方面源于来自官方的打破法兰西民族文化古希腊-罗马起源观,构建以凯尔特文明为内核的当代法兰西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需求,一方面又与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各省编制档案用于乡村治理的理念有关。尽管学会成员的知识背景较为庞杂,但其编制的民俗调查问卷内容较为详尽,分类较为清晰,体现出较高的对民俗事象的认知、分类和归纳水平,对后来法国和德国的民俗学研究的方法、对象和目的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客观地说,凯尔特学会为半个世纪后法国民俗学的真正成型作了部分方法论和研究资料的准备,但尚未产生较为学术化的研究成果,因而可以被视为法国民俗学的筹备阶段或史前史阶段。
一般而言,欧洲国家早期的民俗学(在某些国家又被称为“自我民族学”,即auto-ethnologie)都有像历史学一样构建本民族“神话”(mythe national)的作用,都像历史学一样把过去作为研究对象,当前存留的材料被用于重构对过去的认识。这也是凯尔特学会和后来的塞比奥、山狄夫等民俗学家的研究目的。通过民俗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学者为本民族认同的构建提供合理性,并“自然”地形成“民族学的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e)。欧洲无论在19世纪末还是20世纪末都不断出现这类学术-政治建设。不过与19世纪初的凯尔特学会不同,后来的民俗学对于法国的影响更多地在于对地方主义(régionalisme)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推动上,对地方认同的促进超过了对法兰西民族国家认同的促进。
参考文献:
Arnold van Gennep, ed., Manuel de Folklore Français, Paris, Auguste Picard, 1936.
Aux origines de l’ethnologie française : l’Académie celtique (1804-1812) et son questionnaire (1805), http://www.garae.fr/spip.php?article227
Bottin, secretary general, « Rapport»,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2 (1820).
Claudine Gauthier, Histoires croisées – Folklore et philosophie de 1870 à 1920, Lyon, 2013.
Du Bellay, Joachim. La 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Gallimard, 1994.
Harry Senn, “Folklore Beginnings in France, the Académie Celtique: 1804-1813”,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Vol. 18, No. 1 (Jan. – Apr., 1981).
Harry Senn, « Gaston Paris as Folklorist (1867-1895):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French Folklore Studies »,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12:1(1975):47-56.
Jean-François Gossiaux, “Du folklore à l’ethnologie française », version française inédite d’un article publié en italien. Référence de publication : 2000, « Dal folklore all’etnologia francese », in Michel Izard et Fabio Viti (a cura di), Anthropologia delle tradizioni intellettuali : Francia e Italia, Roma, CISU (Quaderni di etnosistemi).
Académie celtique,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celtique, tome I, 1807.
(引证以刊物为准,注释参见原文,《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
栏目主编的邮箱:yunafk929@163.com
公号公共邮箱:folklore_forum@126.com(这个邮箱请注明新青年)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
新
●
青
●
年
专栏连载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中国民俗学会 · 业务范围
理论研究 学术交流 业务培训
书刊编辑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中国民俗学会
微信号 : ChinaFolkloreSociety
微信订阅号:民俗学论坛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民俗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