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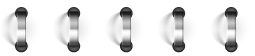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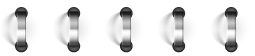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孟凡行,男,山东寿光人,民俗学和人类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人类学、艺术与文化遗产、民俗艺术与乡村发展。本文认为“非遗”表达的是群体性的生活理念和理想追求,是一种群体性文化。“第一群体”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核心力量,但由于其不是“非遗”保护的唯一群体,其利益和理念也就不是唯一的,还应该照顾到更大群体或其他群体的诉求。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生态问题上,意识到“非遗”是一种生活性的文化,具有很强的生态性。任何“非遗”项目都有一个生态性的技艺链和生活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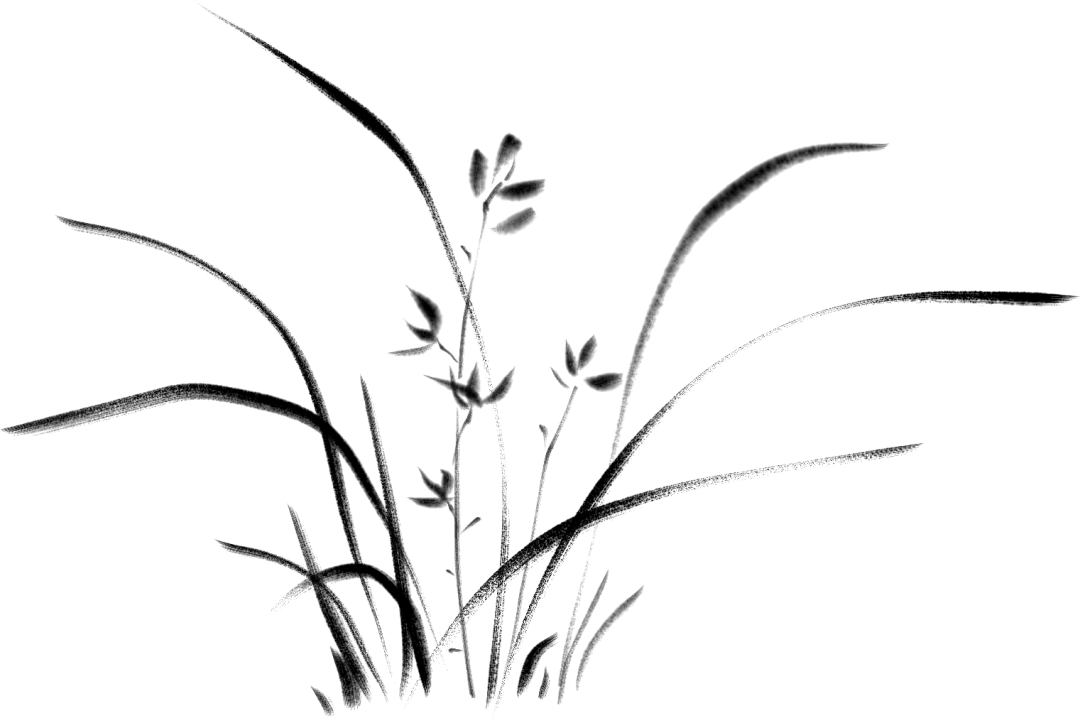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第一群体”及其生态扩展
孟凡行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
2021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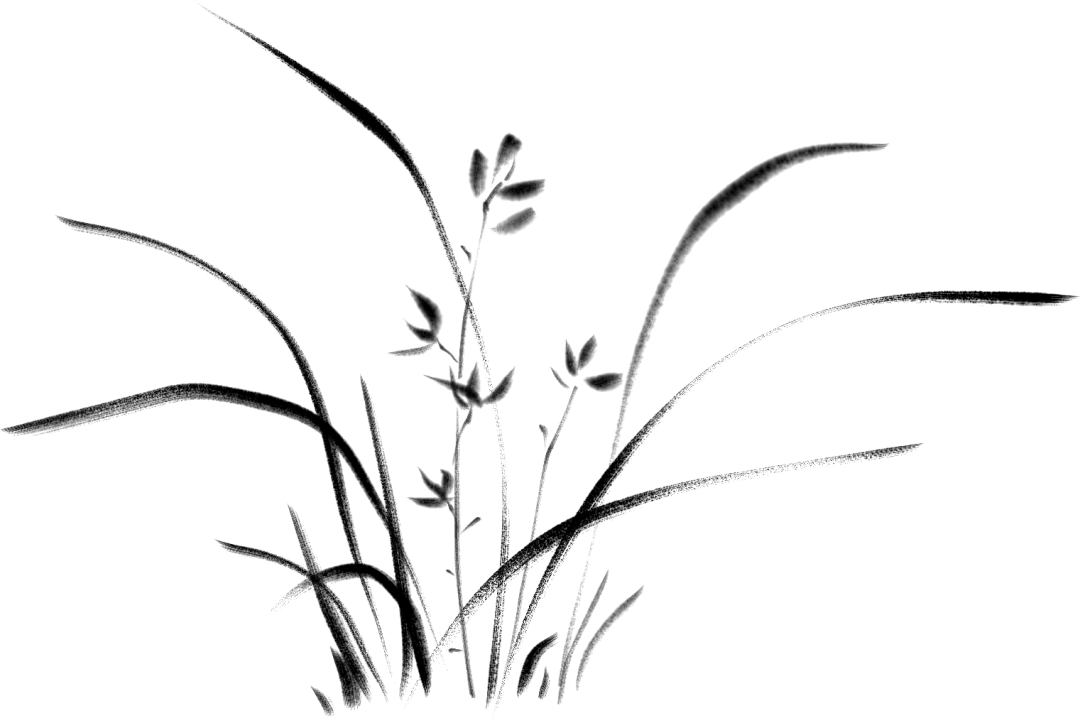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届常委会,针对各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在道德层面、立法层面或是商业利用层面出现的对“非遗”的滥用和不尊重等问题,于2015年审议并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以下简称《原则》),特别强调了社区、群体和个人在保护和传承“非遗”中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在2019年发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在“非遗”保护和传承过程中要“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注重社区和群体的认同感”。这一内容在2008年发布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中是没有的。可以说是国家层面针对十余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和传承中出现的对“非遗”传承人、特别是对“非遗”传承过程中有损社区和群体认同的问题做出的调适,也可以看作是对《原则》的一种呼应。

“非遗”表达的往往是群体性的生活理念和理想追求,因而是一种群体性文化。这种文化由群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累积而成,也由群体来传承,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爱好、天赋秉性等原因会出现“大大小小”的优秀传承人,但其“大小”是在群体内部的自然互动中形成的,“非遗”保护政策对这种局面造成了一定的改变,有时候会造成“围绕传承人的指定而导致的亲朋邻里间的不睦”。“非遗”的群体性也不同于现代文学和艺术创作对个体性的追求和强调。但在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理念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不少“非遗”传承人追求个性创作和创新,追求艺术家的身份(这种行为甚至受到“非遗”行政人员、学者等的鼓励),从而导致作为群体文化代表的“非遗”传承人的身份弱化,“非遗”作品群体性降低。一方面使“非遗”作品的特性受到伤害,另一方面亦使原本由群体积累的“非遗”资源走向个体消费,从而破坏了“非遗”所在社区、群体的微权力生态,降低了社区和群体的文化认同。
由于“非遗”是群体性的,也就没有个体性的“非遗”一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非遗”文件中的“个人”是从非遗保护实践的操作层面来说的,而非指存在个人性的“非遗”项目。由此可见社区、群体对“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则》和《管理办法》的出台是非常及时和切中要害的。但值得讨论的是,《原则》和《管理办法》对“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社区、群体的表述过于简约。特别是《原则》,对社区和群体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中的作用强调得过于绝对,比如第六条“每一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所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的价值或意义评判”。姑且不论是不是所有社区、群体,甚至个人能否完全认识到所持有的“非遗”的价值,只说很多“非遗”项目是跨社区、跨群体,当然更是超越个人的,身在其中的社区、群体、个人由于见识的限制和利益的考量不可能对自己所持有的“非遗”做出公正的评价。最有可能出现同一种类的“非遗”不同持有者众说纷纭,都强调自己的优于他人的结果。此既不利于“非遗”的整体性保护,也会伤害到社区内部、社区之间的认同和和谐。更不用说会导致社区主义式的对“非遗”普遍价值的漠视了。
众所周知,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非遗”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及方法受人类学和民俗学影响很大。而现代人类学和民俗学普遍重视田野调查,这种调查又大多以社区和群体为中心展开。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20世纪末学术界掀起了全球化研究热潮,全球化的事实和知识界、传媒界对全球化意识的强调在使地球变为“村落”的同时,也引起了各地对全球化的警惕和抗争,地方化随即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另一面。在理论资源方面,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茨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但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并非着眼于地方,他说“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可见,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的重点是“地方性”而非“地方”,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对地方文化的深描和阐释找寻人类文化普遍性的东西,这仍然是人类学家对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最终追求。由于格尔茨在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巨大影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也大多实践了一种“小地方,大社会”“小切口,大问题”式的研究路径,而较少考虑所研究的社区、群体的层级或次序问题。

田野研究者在考察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被以下问题困扰: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什么?为了谁?应该对谁负责?等等。既然是学术研究当然是为了学术。那学术研究又是为谁服务?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自然是为天下,为全人类。这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田野考察依靠谁?当然是被研究者、被研究的社区和群体。这就又带来一个田野研究的服务对象问题。田野研究的服务对象并非是一个模糊、虚幻的全人类,而是若干属于不同层级的群体,比如信息提供者、信息提供者所属的群体、群体所属的共同体或社区,与之有关系的更大的共同体或社区,以至国家、世界等等。无论中间有多少层级,信息提供者及其所属的共同体,比如村落或者行业群体都是第一群体。
不管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还是《原则》,均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社区、群体作为“非遗”持有者的唯一群体看待。学界在解读和评述上面两个文件的时候,大多也是这样来理解的,从而体察到了“非遗”保护的内部和外部的张力,也认识到了由此带来的有悖于“非遗”整体性保护的诸多问题。若从整体论和生态学的观点来看,“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群体是有层级的,《公约》《原则》《管理办法》中的群体其实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第一群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约》和《原则》中的核心词community指的不是有着特定地域范围的社区,而是文化共享意义上的共同体。本文所用的群体概念也倾向于建立在文化共享意义上的共同体而非社区。有的共同体在一个社区内,有的跨社区,但两者的重合度确实比较高。从有层级的群体和“第一群体”的理念出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可较好地在充分理解《公约》和《原则》的基础上,进行“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本土实践。由于“非遗”持有者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第一群体,其利益、理念自然应该得到优先关照。但由于其不是“非遗”保护的唯一群体,其利益和理念也就不是唯一的,还应该照顾到更大群体或其他群体的诉求。这就不存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内部和外部的分野了,因为各利益相关方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毫无疑问,“第一群体”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核心力量,但他们却不一定能认识到“非遗”的全部价值,尤其是“非遗”所体现出来的人权、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等普遍价值。比如哈尼族的“‘哈尼哈巴’是一个全民族共享的宏大口头文类,这个认知主要是从事口头传统研究的少数学者具备,大多数哈尼族歌手并不具有这个认知”。笔者在不同的地方调查,也常感受到,不少“非遗”传承人,甚至国家级的传承人对“非遗”的普遍价值的认识多停留在口头和表面上,其最关心的还是其经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排除其他群体和力量的影响,完全由“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第一群体”来评定“非遗”的价值是不现实的。这一原则得到较好贯彻的基础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第一群体”具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评判和传承“非遗”的能力,但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公民的视野、现代意识、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这个愿望的实现恐怕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目前的问题如何解决?被称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在研究和实践如何将国外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中国落地时,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外国学者坚持一开始就将文化的评判、解释、行使权交给村民,效果很不理想,因为作为文化主人的村民并不理解生态博物馆的先进理念。苏先生就此提出一个理念,谓之“文化代理”,也就是说在文化传承的“第一群体”还没有能力行使其权利的时候,需要由政府、学者、文化持有者组成一个临时的群体,代为行使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职责。现阶段的“非遗”保护和传承亦应作如是观。
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文化代理阶段,最为关键的是想办法让“非遗”传承不中断。这就牵扯到“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生态问题,因为“非遗”是一种生活性的文化,具有很强的生态性。任何“非遗”项目都有一个生态性的技艺链和生活场景。传承者和欣赏者若意识不到这一点,那就必然会把“非遗”当作一种展演的艺术作品来欣赏了,但绝大多数“非遗”“产品”的艺术性是难以和相同种类的艺术品相比较的,这就给欣赏者造成了一种“非遗”技艺不够精湛、美感不足的感觉。这需要扭转一种观念,即“非遗”不是用来审美静观的,而是用来体验的。

近几年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将“非遗”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的。“非遗”传承人也好,“非遗”产品也好,仅仅是“非遗”的一个片段,而观众对“非遗”片段的欣赏本身就是对“非遗”整体的误读,这种误读反馈到传承人和社会层面又造成了对“非遗”的破坏。彭兆荣教授团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在四川美术学院开展的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活动,采取了“校园”和“非遗”“双向走对”的模式,师生先走进“非遗”原生地体验“非遗”,然后“非遗”传承人再“回走”校园,“非遗”传承人、学者、学生在平等、真诚、互学的氛围中对话,使手工艺的地方价值和基于生命史的普遍价值均得到了关照,从而实验了一种“非遗”传承的新模式。
在这种“双向走对”的“非遗”研习和传承活动中,着重注意的就是充分尊重处于“非遗”传承第一群体核心位置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对自己文化的实践、理解、要求和讲述,在此基础上挖掘“非遗”的普遍价值。鄂伦春族兽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满古梅在讲述本民族手工艺的时候,将鄂伦春族的山川河流、祖先神灵、生产生活都带出来了。这启发我们,手工艺只是鄂伦春族的一个民俗标志物,这种手工艺与现代意义上自律的艺术不同,我们只有在作为整体意义的鄂伦春历史文化生态中才能充分理解它。这也是所谓活态遗产的整体论意义,即通过一个共同体的标志性“非遗”看到的是这个共同体的全部,而不仅仅是被抽离出来的一种技术、一类物品。从传承的角度来看,借助这类手工艺的手工实践所形成的经验,可踏向通往一个共同体的人文世界之路。
现在不少传承人和学者强调手工艺的经济、技术和地方文化史价值,笔者在参与这次活动中,着重强调了其对于人类接近传统人文世界的经验价值。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生物机体的缓慢进化可能是未来人类长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怀旧、乡愁、欲壑难填、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均是这一矛盾的表层显现,这只能依靠居于其间的人文思想来调适,而传统的人文思想无疑是新思想的主要源泉。本雅明认为接近传统的唯一途径是经验,而传统社会是一个“手工文明”(彭兆荣语)社会,其人文思想建立在手工劳作的基础上,比如传统人士大多奉行“耕读传家”的理念。若要对传统人文思想进行深度理解,恐怕离不开手工经验。机器大工业以来,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日益分化,前者大多脱离手工劳作,后者也越来越走向机械化,整个人类也就很难体认手工文明的价值,把握手工文明的内涵。
鉴于此,笔者对参与本次活动讨论的研究生们最关心的“究竟如何传承手工艺”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进入手工艺“第一群体”的生活场景,体验其生活,最重要是动手做。通过手工操作接近传统的人文世界,创生新的人文思想,这便是手工艺的普适价值。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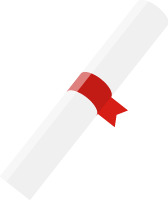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95.新青年|赵元昊:从淮阳泥泥狗观察民间艺术存续的文化生态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