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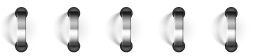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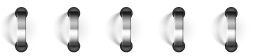

本期新青年高志明,男,汉族,河南项城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博士,周口师范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神话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本文以神话分类为中心,简要说明“叙”和“事”两种研究取向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尝试以“存在形态”这一属于“叙”的范畴对神话进行一种新的分类,并讨论这种分类的结果和意义。
高志明
2020年第5期
神话本质上是一种“叙事”,“叙”是讲述的形式,“事”是讲述的内容,历来多数的神话学研究都集中在神话的内容上,就神话的分类而言,基于神话内容的分类远远早于并多于基于形式的分类。神话经由何种媒介讲述,或者说神话存在的载体是什么,是从形式范畴认识神话的一种路径。“存在形态”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既包含事物的即时静态,也包含事物可能的发展动态,能反映事物的综合面貌。以存在形态为依据,可将神话分为:书面神话、口头神话、仪式神话、物象神话、演艺神话、新媒介神话等,这些类别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经过界定可以网罗当代语境下神话的各种存在形式。这种分类方法在扩充神话分类体系、增加神话研究维度的同时,还具有彰显神话学学科的现在性、确保神话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以及促成神话研究方法的革新等方面的意义。

关于神话的界定,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人们界定神话的目的自然是更为清晰地认识神话,每一种界定都在某个维度上力求揭示神话的本质。然而关于神话的认识如此因人而异,以致于常常造成学术讨论的难以通约,于是关于神话定义的“最大公约数”也便成为一个问题。学者杨利慧在其著述中引述过一则美国民俗学家斯密斯·汤姆森(Smith Thompson)于1955年对神话提出的一个所谓最低限度的定义:神话所涉及的是神祇及其活动,是创世以及宇宙和世界的普遍属性。然而,对这一“最低限度”的界定,仍有人并不认同,如在神话学者李子贤看来,神话所涉及的并非都是神祇及其活动,“与神祇的活动无直接关联的神话,大量存在于国内外的许多民族之中”,考之中外神话,确乎如此。由此,史密斯·汤姆森的这一“最低限度”并未达到最低。
在对神话的定义中,常见的模式是“神话是关于……的叙事”,研究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神话是关于什么的”,而对这一判断句式的宾词“叙事”从无人怀疑,故而,如果真要求取神话定义的“最大公约数”,或许它只能是:“神话是一种叙事”。当然,能够叙事的不只是神话,很多文类都在叙事,但这不影响神话作为一种叙事现象存在。
既然学人普遍认可神话的叙事性,那么“神话的本质就是叙事”这一判断也是成立的。其中,叙事的“事”是神话的内容,即神话讲述什么,“叙”是神话的讲述,即神话如何讲述。由此,神话区别其他叙事文类的差异便在这“所叙之事”与“所行之叙”上,也就是说,神话“所讲的是什么故事”以及“如何讲述这些故事”决定了神话与其它叙事文类的差别。相应地,如果我们能从“讲述什么”和“如何讲述”这两个方面入手,研究这两方面的特殊性,我们关于神话的认识便可能有所深入。下面以神话分类为中心,简要说明“叙”和“事”两种研究取向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尝试以“存在形态”这一属于“叙”的范畴对神话进行一种新的分类,并讨论这种分类的结果和意义。
各国对神话叙事的研究几乎都有一个漫长的以“事”为主的阶段,对“叙”的关注则出现得相当晚近。历史上,关于神话“所叙之事”的研究比比皆是,从古希腊的“欧赫美尔主义”“寓意说”等开始,一直到近世的自然神话学派、比较神话学派等,乃至更为晚近的心理学派、结构主义学者等影响深远的学说,大都不遗余力地去解决神话究竟讲了什么、故事背后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而从19世纪的神话仪典学派开始,学者们才更有意识地关注神话是如何演述的,此后功能主义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等均不同程度地聚焦于神话的讲述本身,而更为晚近的表演理论则是纯粹以故事如何讲述为中心的,在这些学说的影响下,学界对神话叙事之“叙”的关注也蔚然成风。在这样一个宏观的学科背景下,研究者们关于神话的分类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历程,即从一开始主要以“事”为依据进行分类,且属于“事”这个范畴的分法至今仍常见不衰,而以“叙”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出现得相当晚近。
1、属于神话内容范畴的分类
分类是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对神话进行分类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分类首先是要有分类标准的,因为神话“所叙之事”的直观性,多数神话学者均以神话的内容为依据对神话进行分类,世界范围内多是如此,这一现象从东亚三国颇具代表性的研究那里可见一斑。
中国神话学发展早期的学者对神话的划分多基于神话讲述的内容。以对中国神话学影响深远的茅盾为例,他在1929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神话研究ABC》中分述了六种神话:(1)天地开辟神话:(2)日月风雨及其他自然现象的神话;(3)万物起源神话:(4)记叙神或英雄武功的神话;(5)幽灵世界神话;(6)人物变形的神话。这六种神话区分的依据颇为明显,乃是故事所述内容的不同,具体而言,显然是发生在不同叙述对象身上的不同故事。在茅盾之后,黄石、林惠祥、谢六逸等人对神话的分类无一不是以内容为依据的。
日本学者大林太良对神话的分类也是典型的以“所叙之事”为标准的。大林太良在1966年的著作《神话学入门》一书中,提到德国民族学家卡尔·施米茨关于神话的三个基本问题:是谁用什么方法创造了世界?是谁用什么方法创造了人类?是谁用什么方法创造了文化?然后他以此为基础将神话分为三个类别:(1)宇宙起源神话;(2)人类起源神话;(3)文化起源神话。这是一种概括性很强的神话分类方法,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如韩国学者崔仁鹤、中国学者杨利慧等都在著述中沿用过这一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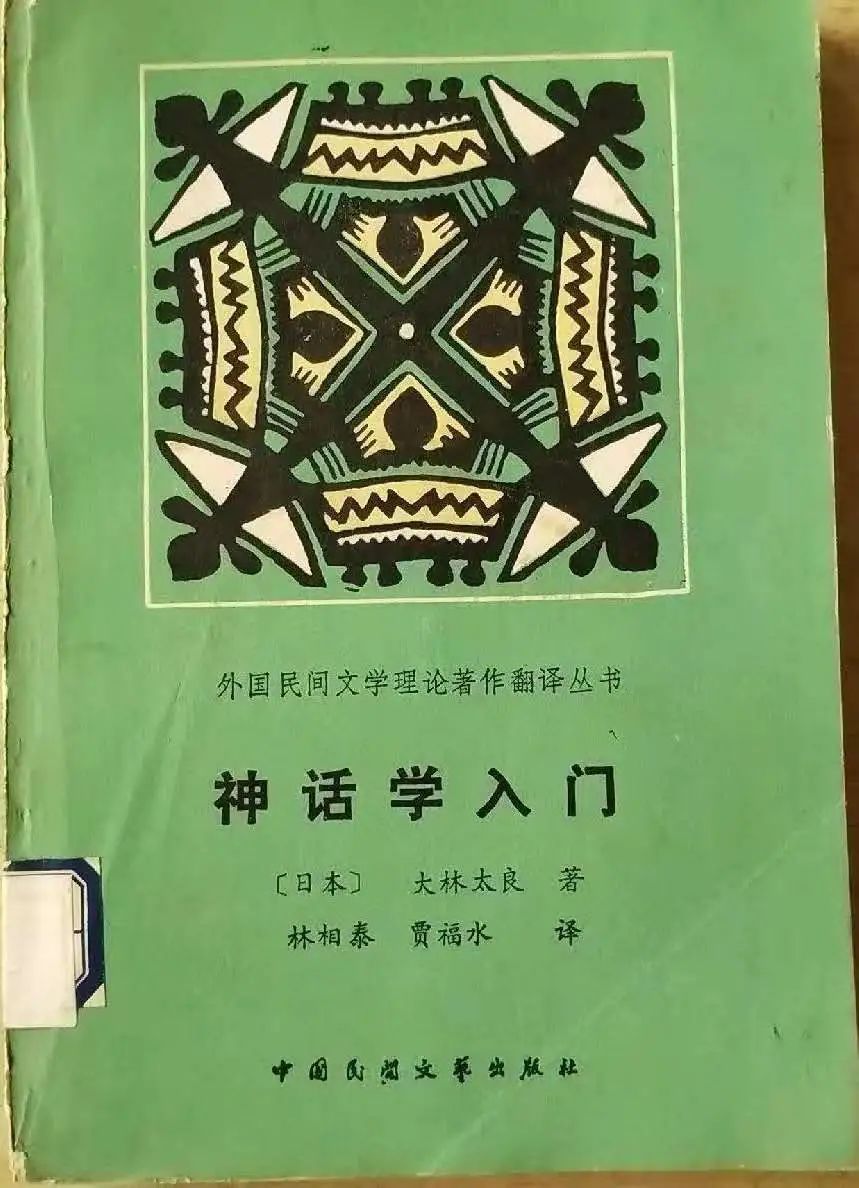
在韩国比较常见的神话分类,从本质上讲也多属于依神话内容划分的范畴。如根据故事主人公的不同社会地位可将神话分为为:王朝神话、家族神话、部落神话、巫俗神话;根据神话流传范围的大小,分类结果为:建国神话、始祖神话、部落神话、其他神话等。其中,作为分类依据的主人公自然是故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传范围与神话中的主人公在国族历史上的地位高低有关,且从“建国”“始祖”等字面上也容易让人联想到神话叙事的内容。
从以上东亚三国的情况看,学者们往往以神话内容为依据进行分类,虽然不断有人提出新的分类方法,但也仅是角度不同而已,可见,以故事内容本身或本质上属于内容范畴的分类依据在学界深入人心。
然而如大林太良所言,“神话的确也是故事,但正如施德尔所指出的那样,神话要高于故事,故事即使是神话表现形态中最重要的,但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这就是说,神话除了故事内容本身外,还有其他很多方面需要研究者予以关注。
2、属于神话形式范畴的分类
在经历了长期以神话内容为依据的分类之后,随着学科大背景的转换,各国纷纷有人注意到神话的讲述形式也可将神话区分开来,于是区别于以“事”为中心的分类方法陆续登场。在中国迥异于以前的分类方法也不断涌现,单以“形态”二字为依据的分类就有多个。
学者陈建宪认为神话有四种形态。按照陈建宪的观点,神话从遥远的古代产生之后,就成为各民族精神行囊中最宝贵的遗产,一代代的人们不仅反复复制着祖先们创造的神话,而且自己也不断创作着新的神话。与此同时,神话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神话,其实是“一种许多世代层层积累起来的沉积岩”。它们的形态,归纳起来大约有下述四种类型:(1)原生态神话,是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及其以前的初民所创作和讲述的神话;(2)再生态神话,产生于原始氏族公社及其以前时期,但流传于这一时期之后;(3)新生态神话,产生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以后的各个时代中,直到今天仍在不断产生;(4)衍生态神话,是上述三类神话在其他领域中运用和改编的衍生物。这种分法主要考察一则神话是源还是流,并不关心它是什么情节,摆脱了以神话内容为依据进行分类的惯例。
向柏松在其著作《中国创世神话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一书中,将创世神话分为三种:原生形态、衍生形态和系统形态。其中原生、衍生之名或是延用了陈建宪的提法,但内涵却不尽相同。向氏的原生形态指的是时间序列上产生最早的单一释源性神话,并且他认为单一释源神话势必向系统神话演进;系统神话是高级形态的神话,是完整解释世界起源、人类起源、文化起源的综合性神话;而从原生形态向系统形态过渡的中间形态被其称为衍生形态神话,这又明显不同于陈建宪所言的衍生态神话,陈氏的衍生神话是后世关于神话的各种借用化用及由此产生的变体,在时间上是最后产生的神话,而不是处于中间阶段的神话。虽然向氏在本书中的关注点只是创世神话,但他的分类结果俨然也可对应于非创世神话。然而他的分类存在的问题,与陈建宪的一样,都是在于主观划分了各类神话的前后演进顺序,事实上,各民族神话并非都是沿着他们提出的前后阶段直线演化而来的,反过来说,如果神话演进的历程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基于这种假设的分类法本身也就立足不稳了。
在文日焕和王宪昭合作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概论》中,他们明确提出了按照“形态”对神话进行划分的方法。为此,二人专门对作为分类标准的“形态”一词做了说明:即指神话的外在的可以观察和体验到的形式。在这部神话概论中,文、王师徒将神话分为:民间口头神话(也称之为活态神话);文献神话;文物神话(岩画、雕刻、绘画、服饰、宗教器物);民俗中的神话(民间祭祀、集会等)。二位的高明之处在于进一步跳出了故事情节的迷雾,避开了故事内容雷同、情节交叉给分类带来的各类别之间界线模糊的弊端,而根据神话出现的场合或载体将之区分成不同的类别,这显然解决了以内容为中心的分类结果中区分度不明显的痼疾。


很明显,上述三种分类方法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实现了对神话内容的超越,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再着眼于神话具体讲了什么,而是从神话怎样讲的角度对不同表现形式的神话做出了区分。所不同的是,陈建宪和向柏松的分类方法是历时的视角,以充满进化论色彩的眼光将各类神话放入他们认为的历史序列中去,不但对神话做出了分类还为它们安排了产生时代;而文日焕师徒的分类方法是共时的眼光,忽略神话的产生时代问题,只把存于不同载体上的神话做出区分。而以上述三种分类方法考之于当今的神话,则又存在更大的问题,他们的分类都没有网罗住当下所有的神话形态。
在上述对神话形态的分类之外,也有学者对神话的存在形态进行了研究。事实上,以云南大学李子贤教授为主的关于神话存在形态的探讨,比之单以形态为题的神话论说要早,也因此之故,对神话“存在形态”的分类也早于单纯对神话“形态”做出的分类,而且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具有着不同的学术思考方向,陈建宪、向柏松之神话形态侧重神话的动态演化,王宪昭所说的神话形态与李子贤的存在形态更为接近,侧重神话的载体形式。
在详细解释本文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存在形态”一词,即以其作为神话分类标准的合法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李子贤关于神话存在形态所做的研究,以便再此基础上讨论“存在形态”一词的确切内涵及其对理解神话具有的特殊意义。
1、李子贤的神话形态论
李子贤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国内第一批关注神话存在形态的学者,在此领域颇有建树。他在《活形态神话刍议》(1989)一文中,将神话分为三种:(1)活形态神话,即与特定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保持紧密的有机联系,并被人们视为“圣经”而具有神圣性、权威性的神话;(2)口头神话,至今仍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流传、以口头文学为其存在形态的神话,这类神话与上述种种联系逐渐丧失,而以人们口头流传为特征;(3)文献神话,即笔录的以书面“作品”形式为其存在形态的神话,是一种“僵死”的神话,被制作成标本的神话。这是国内所见最早以存在形态来区分神话不同类别的尝试,虽然这种分类方法本身被其所倡导的活形态神话研究的光芒所遮蔽,但它不失为一种神话分类方法的新发展,体现了神话分类标准从内容范畴到形式范畴的扩展。
在新进的“活形态神话新论”中,李子贤发展了其早期对神话的三分法,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四分法。他认为神话至少有四种存在形态:(1)文献神话或书面文本神话;(2)口头神话;(3)活形态神话;(4)以某种实物或虚拟物为象征符号及载体的神话。在这四类中,口头神话与活形态神话之间存在某种交叉,对此他专门做了辨析:所谓活形态神话,“是与某种特定的地域环境、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价值取向信仰体系、祭仪系统、思维模式、文化心理以及生活习俗等文化要素融为一体并保持着有机联系的神话。……黏合着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文化要素,在人们的民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中发挥着某种功能,可视为一种处于某种流动状态的‘活体’”。而口头神话也具有活形态神话的某些特征,“也可以纳入活形态神话的范畴,但并非是一种典型的活形态神话,因为它已与相关的信仰体系、祭仪系统逐渐脱节,正逐步蜕变为一种只是讲一讲的故事。”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鲜活地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人们所必需并被沿习、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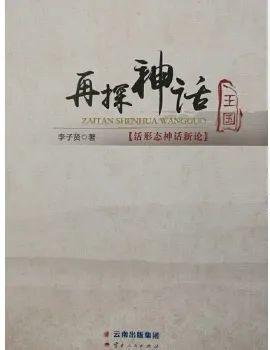
不难看出,李子贤的分类紧紧扣住了“存在形态”一词。他以一种共时的视角,将存在于不同形态中的神话进行归类,同时说明相关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的衍生或转化关系。这种分类没有纠结于各形态产生的历史时期先后的问题,相反,他对“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的代表——活形态神话的重视,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当下的学术情怀,或许正因为此,他的分类才像是从一个时间的横切面去观察神话是如何存在的。
同为老一辈学者的马昌仪先生在谈到神话存续的问题时,也在不经意间以存在形态的差异对神话做出了分别。她在《中国神话故事》(1996)一书的前言中写到,神话通常以三种方式得以保存,第一种方式是保存在文献典籍之中;第二种方式是保存在民间的口头上,活在民众的记忆里;第三种是以实物的方式保存,如岩画、壁画、画像石、出土文物等。马先生并不是有意要对神话做出分类,她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神话借以保存的方式,而所谓保存的方式,说到底指向的是神话的载体或媒介,这都可归为本文所说的“存在形态”的范畴。
2、作为分类依据的“存在形态”
到底何为神话的存在形态?笔者以为,神话的存在形态是指神话故事赖以存留的载体形式、借以流传的媒介形式,及被人认知时的外在表现方式。它首先不是神话所讲的故事本身,也不是神话异文之间的相生相离关系,也不是神话故事情节的内部结构,而是神话故事以什么外在形式存在或以什么方式讲述的问题,它属于神话的形式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的“存在形态”一词是基于汉语语境而言的。在汉语词汇中,“存在形态”是偏正结构的短语,语意重心在“形态”二字,“存在”是对“形态”的限定。就二词语意的繁简来说,“存在”相对而言词意单纯,可以简单对应于英语的“be there”,而“形态”一词的语意则较复杂,可对应英语morph;state;form等词。英语morphology的中文翻译是形态学,其中的morph最初只是生物学的术语,后来被语言学借用,但意义有所转换。英语morph对应的汉语“形态”,在生物学意义上,是指物种的不同变体,对于神话来说大致可对应为异文(version);在语言学意义上,指的是词素,对于神话而言大致可对应为母题(motif)。不同于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中的“形态”取法于语言学意义上的morph,本文所言“存在形态”之中的“形态”一词,与英语世界里morphology中的morph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如果一定要将它对应于英语词汇的话,或许state或form更接近于它的汉语含义。
单就汉语中的“形态”一词而言,它是并列结构的合成词,是由单音节词“形”和“态”组合而成的现代双声词,二字都是对事物外在形式的指称,但它们的含义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源自它们在古汉语当中的本意。
文献中关于“形”的解释虽有多种,但它们从根本上来说是相通的。《说文》中说“形,象形也”,《礼记·乐记》有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庄子·天地》中说“物成生理谓之形”,《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形者,生之具也”。从这些解释中可以得出,“形”就是事物的外形、外貌,是事物天然生成的外在表现形式或所依存的承载介质,它具有稳定性,是事物被人感知时刻业已固化或稳定下来的存在形式,是事物在某个时间点上的静态外观。
“态”的本意也很明确。《说文》对态的解释为:態(繁体字),意态也。段玉裁注曰:“意态者,有是意,因有是状,故曰意态。从心能,会意。心所能必见于外也。”可见,“态”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表现,取决于内,而表现于外,就人而言,内心有所变化则外在表现亦会随之而动,对物而言,内在结构肌理有所变化则外形也或随之而变。可见,在“态”的字义中天然有静有动,本身就是静止状态和发展态势的复合体。
由此,“形”和“态”二字相加,构成了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的“形态”一词,而它也就兼有了二字的复合含义,用它来描述事物时,既直接指向事物的瞬时静态,也隐约指向其可能发生某种变化的即时动态。“形态”再冠以“存在”,便是描述事物如何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存在形态”一词了。
以存在形态的视角来观察神话,能发现神话的更多形式。神话作为一种叙事,根本上是由各种各样的文本表现的,但叙事又不受文本的局限,也就是说,神话本质上是故事,而故事具有独立性,独立于它所运用的媒介和技巧。所以神话可以是书面文字,可以是日常口语,还可以是某种实物、图像、造型,乃至仪式、舞台剧、影视剧、电子游戏等文本形式。既然神话在当代语境下,有如此多的表现形式,我们的分类体系也须与时俱进,将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神话都纳入我们的视野,这样我们对当今神话的分类才算完整,对神话的认识才算全面。
存在形态可以作为神话分类的一个标准。既然存在形态的涵义中含有静止的形式,又兼有流动的态势,那么,以它来观照神话,就能区分出形式固定的书面神话、图像神话、雕塑神话等,变动不居的日常口头神话、仪式中的神话、舞台上的演艺神话,以及动静结合的电子媒介中的神话等,从而实现对各种形态神话的全面把握,进而描绘出当代社会中神话存在的真实图景。正如青年学者高健所言,“一个事物的存在形态既包括它的外在表现形态,也包括其内部各元素的结构性变化,对神话存在形态的区分能够呈现出神话自身的差异性,并且能够从内部分别把握与神话相耦合的文化元素。”与本文所述略有不同的是,他对事物存在形态的理解包含了事物内部的结构,而本文所言的存在形态仅以事物以何种外在形式存在为要旨。做这样的限定,目的在于减少该词作为关键词的义项,避免一词多义带来的分类标准的模糊或不统一,从而便于在一个维度上对神话进行有效地分类。
依据上述分析,存在形态作为一种形式要素最终能反映神话的某种本质属性,故而可以作为区分神话类别的一种标准使用。当然,任何分类都可能存在区分度与网罗度难以两全的风险,对于神话这一复杂文化事象的分类更是如此。以存在形态为依据的分类虽然能囊括当代社会中各种形式的神话存在,但由于汉语词汇语意的多向性,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类别划分完毕之后,仍有必要对各类神话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一番界定性解释。
1、分类的结果
按照神话的存在形态,笔者将神话分为六种:口头神话、书面神话、仪式神话、物象神话、演艺神话、新媒介神话,承载它们的媒介分别是:口语、文字、仪式、实物、表演行为和网络。
口头神话指人们日常生活中以散文形式讲述的神话。这类神话是纯粹的日常口头叙事,与信仰、仪式等未必有直接关联,多数是可以随便讲一讲的故事。口头形态是最为常见的神话形态,田地间、火塘边、炕头上都可听到,同辈之间、长幼之间均可传讲,而今导游面对游客讲述的神话也属于这一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口头神话是最为可能的神话的本征态,也就是说口语是神话最早产生和传播的基础,这是因为,有了语言(哪怕很简单)人才能思考所处世界的起源,才能编织出释源性神话,神话再经由语言交流,人群对世界的认识才可能趋同,然后才可能发展出仪式、壁画或文字等其它形态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口头神话当是神话的原生形态。
书面神话指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神话,是神话的一种派生态。神话的书面形态往往是对某一次日常讲述或仪式唱颂神话的文字记录或改写,文字派生于口头语言,因此书面形态是一种派生态。需要说明的是,书面神话表面上看处于派生地位,似乎没有能动性,而且故事被写成文字便失去了生机,成为神话的僵死标本,但也恰因其是标本才能脱离其原来的民俗生活和文化语境的束缚,使得超越时空的神话传播和传承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若干年前形成的书面神话一旦被放入后世合适的文化生境中,标本里蕴含着的文化基因便可复萌,神话便会以某种新的形式“复活”并开始新一阶段的传承。这一过程实现了书面形态对其它形态的反哺,因而书面神话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僵死的。

仪式神话指寓于仪式中的神话,也是一种复合态的神话。仪式神话可能是由巫师或长老一类的特殊人物讲述或唱颂的,也可能是用其他行为展示出来的,且通常与信仰密切关联在一起。如果仅从口头讲唱的部分看,仪式神话与口头神话在媒介层面上确有交叉,但之所以区分二者,是因为仪式神话必然伴随一定的仪式而存在,它与仪式是二元一体、难分彼此的,仪式是神话的载体。而口头神话作为散体叙事是可以出现在日常生活中随意场合的,这就迥异于仪式神话往往存在于庄重严肃的、约定俗成的、具有广泛认同的生活程式之中;且从表现形式上看,仪式神话在语言之外也可能用肢体动作、周遭环境来展现,这也不同于口头神话主要以口语为载体。当然,区分仪式神话和口头神话并不排除同一神话故事既可在仪式中展演,也可在日常其他场合中讲述的情况,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其自身具有的变异性就蕴含了同一神话有多种存在形态的可能。
物象神话指寓于实物或图像中的神话。物象形态通常也是一种派生态,它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虚拟物,而本质上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符号,以神话的某个要素象征或指代整个神话故事。关于物象神话独立成类的合理性,大林太良的一番论述颇可为据:“对于接受了神话的人来说,在祭祀、神象和装饰性的徽章中,也清楚地认识到神话的内容。基督教徒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不只是通过圣经,而是通过圣餐和十字架的形象,足以使他们理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全部意义。又如,婆罗洲雅朱达雅克人的圣画,它绝不仅仅是对神话的说明,而是神话的一个独立的表现形态。”其中提到的圣经当是书面神话,而圣餐、十字架、圣画均为物象神话。此外,附会了神话的自然景观和反映神话的人为作品如雕塑、壁画、手工艺品、实物造型等均属此类。

佤族崖画
演艺神话指以戏剧、影视、曲艺等各类型表演艺术展现的神话。这类神话是典型的复合形态,可有口头、书面、仪式、物象等形态的参与,而根本载体是演员的表演行为,所以称为演艺神话,典型代表如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等人的神话剧作。需要说明的是,演艺神话和仪式神话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迥异之处。二者同以人的行为为载体或媒介(一个是表演行为,一个是祭祀行为),若追溯源头的话,演艺神话或脱胎于仪式神话,这可从很多赛神仪式中的表演成分看出一斑,傩戏更是由巫师直接扮演相应的神灵。但两者至少在三个方面差异明显:一是存在的场合不同,演艺神话是纯表演性质的,存在于舞台或片场,外在于日常生活,而仪式神话是一种生活实践,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是生活的组成部分;二是行为主体不同,演艺神话的主体是演员,而仪式神话的主体是祭师一类的人员;三是目的不同,前者属娱乐范畴,追求的是艺术,后者属生活范畴,追求的是功利。
数字神话是以光、电、磁等为介质储存和传输,借助数字技术处理、通信技术传播、特定设备再现的神话。这类神话的主要存在于非纸质介质和网络空间,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网络原创的形式,如根据神话开发的电子游戏、讲述神话的网络直播(视频)、运用神话创作的网络文学(仅指生成期,不包括后续纸质出版及影视改编)等;一种是其它形态神话的数字化、网络化,如将记录或包含神话的文字、图片、录音、视频资料等经数字化处理后放到网上进行传播的形式。数字形态显然是最年轻的派生态,电子游戏、动漫等对神话的运用是神话故事的别样演绎,是数字形态神话的典型代表。而前述五种传统形态进入网络后,虽然内容仍是原貌,但是它成了一种虚拟的信号,脱离了物质载体或取消了现场感,只能再现于屏幕中,故而也称其为新媒介形态。新媒介神话实现了前五种形态神话对时空的更便捷超越,使得神话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进行传播和传承。以目前的发展态势看,神话的数字化、网络化几乎是一种必然趋势。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2、分类的意义
依据存在形态对神话进行分类,对神话学而言,除了增加一种神话的分类标准,进而提供一种把握神话的新视角外,至少还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说明神话学的现在性(nowness)。神话学的现在性基于神话的现在性。神话从内容上来说是关于过去的故事,其中蒙昧的、神圣的成分在当代观念的冲击下显得有些过时,似乎与人的生活渐行渐远,但事实并非如此,神话是一个极具现在性的文类。神话的现在性体现在其天然具有的变异性上,神话的每一个异文都是其所处时代的反映,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有符合其要求的神话讲述。同样地,每一种新形态神话的产生,也都是神话在特定时代的演绎。通过存在形态对神话进行分类,我们发现神话仍然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进入了与之存在某种悖论的科技领域,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进行不断地重述,以全新的形态存在和演绎,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和传承,这就是神话在今天现在性的体现。既然古老的神话仍然存在于当今人们的生活,神话学就有介入当下研究的可能和必要,积极关注日常生活,投身社会现实研究并解决相关问题,如讲好中国故事、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等,是神话学的时代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学也是现在之学、当下之学。
其二,确保神话研究对象的丰富。理想的神话研究对象之一是活态神话,然而即使在知名的活态神话研究专家李子贤看来,随着神话存活的条件(包括传承场、传承人、与神话相关的祭仪或习俗,以及人们对神话的依存度等)的改变,云南神话已经进入了式微期,并且预判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后神话时代”。其实不单云南地区如此,全世界范围都是如此,这是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思想观念变化的必然结果,各地所不同的只是这一进程的快慢而已。面对这样的情形,如果神话研究一直囿于传统的神话观念,经典的研究对象将不断流失,神话学最终将丧失重要的研究阵地,所以要关注神话在当代的新变化、新形态,这样不论神话以何种形式表现或存在都不影响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属性。以存在形态作为标准的神话分类,把神话的多样存在尽收囊中,如此以来,就避免了在传统的讲述或展演消失或转换之后,神话学找不到“理想的”研究对象的尴尬。故此,这一新的分类方法让我们有能力应对世界范围内的“后神话时代”。
其三,呼唤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新媒介无孔不入,各类神话进入新媒介或以新媒介来表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也就是说,新媒介将是各传统形态神话的一个必然宿体,它必将深刻地影响神话传承的形式和方法。随着新媒介的普及,神话内容终将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而人们熟悉了神话所讲故事之后,如何讲述又将成为新的问题,近年来兴起的以IP产业为代表的新业态,似乎正在酝酿生成新的神话讲述方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既然新的分类方法,把新的神话形态纳入到神话谱系之内,这就需要神话学发展出相应的研究方法来应对。杨利慧近年来提出的“神话主义”视角,将电子媒介、导游讲述中的神话等作为研究对象,讨论脱离了原有语境的神话挪用和重述现象,进而探讨神话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延续等问题,这种方法就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大大扩展了神话研究的适用性,是目前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面对神话当下多形态的存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是摆在神话学人面前的历史任务。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楚雄师范学院报》2020年第5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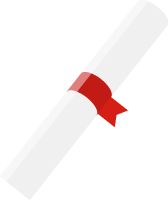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98.新青年|吴玉萍:自媒体与民众日常的价值: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197.新青年|程鹏:规避与规范:民间文学的导游传承路径研究——以泰山传说为例
196.新青年|孟凡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第一群体”及其生态扩展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