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姚丽梅,女,广东惠州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俗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民俗和饮食文化。本文以流行于粤、港、澳等地的“广式老火汤”为研究对象,重回广式老火汤发展变迁的社会语境,发现促使其成为“养生饮食”背后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近年来关于老火汤“是否养生”的争议,思考传统饮食习惯与现代营养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调适问题。
社会变迁中的饮食与养生
——以广式老火汤为例
姚丽梅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19年第1期

摘 要:从日常养生食品广式“老火汤”的变迁历史来看,清末至民国现代工商阶层的崛起引导了新的饮食需求,使“煲汤”成为新的饮食风尚,此为“老火汤”的孕育期;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药膳、商贸、餐饮、图书出版、旅游等多种产业发展的驱动,“煲汤”被有意打造成广东传统养生食品“老火汤”,并在适应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进一步内化成为本土饮食记忆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在现代医学、营养学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改良“老火汤”的烹饪方式,但煲“老火汤”的饮食习惯却依旧传承。由此可见,人们在饮食与养生的选择中,所依据的并不仅仅是现代医学体系下的健康与营养标准,食物的口味、经济利益及文化意涵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对思考当下由传统饮食习惯与现代营养建议之间的冲突而引发的饮食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饮食;养生;广式老火汤
食物的营养与健康是饮食文化研究近年关注的热点论题。不少研究指出,传统饮食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不适应性是当下食品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马文·哈里斯(Marvi Haris)在《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中提到,一些原先符合现代营养学标准的传统饮食方式,可能会在市场经济商业利润的驱使下,被工业产品以不实宣传和营销手段取而代之。林富士在分析台湾嚼食槟榔的食俗时,指出一些有违现代医学健康标准的传统饮食习惯,因长期受文化薰习而形成,仅以单纯的健康论述很难切断其文化纽带。赵旭东则认为,传统饮食文化奉行天、人、食物相互关联的整体思想,现代社会人与食物的关系则是分化和脱离的,这种差异影响了食品安全观念的变革,应当结合传统的饮食认知逻辑和西方现代食品生产与管理机制来思考这种变化。可见,关注传统饮食观念在现代社会如何适应、发展或转变,是深入理解当下饮食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中国,自古便有通过适宜的膳食来调养身体、延年益寿的观念与方法,通常被称为“饮食养生”。中国饮食养生观念生发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医理念,从这两方面探讨饮食养生文化生成机制的论述较为丰富,但却缺少对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养生观念及饮食实践的考察。基于此,本文拟以流行于粤、港、澳等地的养生食品——广式老火汤为例,结合文献材料和调查访谈,从经济生产、商业发展、生活模式、文化传播等多元视角梳理老火汤的发展变迁历史,分析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讨传统养生饮食在现代营养学的影响下“何去何从”的问题。
一、从“羹”到“汤”:
工商阶层的兴起与饮食风尚的变化
老火汤,顾名思义,即长时间用火熬制出来的汤。老火汤有两个重要特色,首先是讲究火候。煲老火汤通常先以大火煮沸,后改用文火熬煨,直至汤料的味道融入汤水之中。广东以往还有“煲三炖四”(“煲汤三小时,炖汤四小时”)的说法,所以烹具一般要选用耐热性高、受热均匀的瓦煲或砂锅。除了火候之外,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讲究性味和节气。老火汤通常以肉类、骨头搭配蔬果、豆类或中药材同煲,在选料上要“五味相调,性味相合”;此外,四季气候不同,各人体质相异,老火汤谱也因此层出不穷,既有“四季老火汤”,也有“滋补老火汤”、“清热降燥老火汤”等,是谓“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岭南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夏长冬短,夏季雨热同期,常给人以炎热潮湿之感,这样的气候容易使人肠胃敏感、消化功能较弱,故羹、粥、汤这类易于吸收的流质状食物在此备受青睐,当地俗语亦称: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岭南常见的汤一般有三类:滚汤、炖汤和老火汤,其中滚汤、炖汤常见于其他各地,老火汤则为岭南人所独衷,尤其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等粤语方言区最为流行。不少粤籍华人华侨还将此汤带出国门,所以又称“广式老火汤”。

关于老火汤的起源,因其多用瓦煲熬煨,讲究性味相和,又多有药材入汤,所以许多学者都将其与中医药膳联系起来。有学者更直接提出广式老火汤实质即口味改良的中药药汤。老火汤的烹制理念确然受到中医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显著影响,旅美华裔陈蓉在《传统之汤:来自中国珠江三角洲的美味》中便详细分析了广式汤水与“药食同源”、“阴阳五行”等中医食疗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古代中医食疗方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与老火汤相似的汤方。如明末清初广东番禺文人何其言在《增补食物本草备考·食治方》中收录的“鲤鱼汤”:“当归、白芍各一钱半,茯苓、白术各二钱,用鲤鱼一个,水煮清汁一盏半,入生姜七片,陈皮少许,同煎至一盏。”但食疗方毕竟以“疗”为主,上述鲤鱼汤便专为“治妊娠五六月,胎水腹大异常,高过心胸”。而老火汤作为大众日常饮用的汤品,与针对性更强的药膳不尽相同。
可见,老火汤虽深受中医食疗思想的影响,但并不等同于药膳。那么,“老火汤”是何时开始成为广东居民的日常饮食呢?徐珂《清稗类钞》曾载曰:“(闽粤人)餐时必佐以汤。”即至少在晚清时期,粤人已经形成了吃饭喝汤的饮食习惯。但结合其他文献来看,清代粤人日常所食之汤应非“老火汤”类的汤品。
首先要了解明清时期“羹”与“汤”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现代,羹、汤二者有明显的区分。一般来说,汤比较清澈,而羹则多将汤料切丝弄碎,再以粉调和,所以更为浓稠。但在古代,“羹”、“汤”经常混用。从字源来看,早期加水烹煮的食物一般称作“羹”,“汤”原指热水,后亦指汤饼(汤面)或中药汤剂。元代始有“羹”“汤”混用的情况,并一直持续到清代。清代广东番禺文人梁松年便曾在《梦轩笔谈》中提到,当时广府人将“饮羹”称为“饮汤”。虽然羹、汤混用,但二者在指称上仍有差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汤即羹之别名也。羹之为名,雅而近古。不曰羹而曰汤者,虑人古雅其名,而即郑重其事,似专为宴客而设者。”可见,“汤”相对于“羹”而言,是一种更加通俗、日常的指称,而对文人来说,“羹”在某种程度上是指比“汤”更雅致、高级的馔食。从《清稗类钞》中也可以发现,虽然不少羹、汤在做法上颇为相近,如作料通常要切丝或切丁、加多种小菜或调料同煮、加粉调和等,但大部分制作繁复、用料精细名贵的菜式,则仍以“羹”命名。岭南文献中有关日常饮食中“汤”的记载寥寥无几,与古代精英阶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价值取向不无关系。
基于这种偏好精致奢华的风尚,古代达官富商在饮食上体现出“尚羹而轻汤”的倾向。从文献资料上看,直至清末,现代意义上的“汤”仍未作为独立菜式出现在广州豪门富户及高级酒楼的筵席当中。在现存年代最早的粤菜谱《美味求真》中,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汤,而是以“羹”或“炖菜”(亦可统称为“汤菜”)居多,如“鸭羹”“燕窝羹”“清炖鸭”“炖水鱼”“炖耳鳝”等。清代至民国初期,酒楼筵席菜单中也极少有汤。如晚清时广州不少酒家推出“满汉全筵”,其中汤类或是如“草菇蛋花汤”之类的简单羹汤,或是随菜配送的“跟汤”。满汉全筵衰落后流行的八大八小、六大六小、十大件、八大件、九大簋等,也只有高级汤菜(如高汤鱼肚)或肉羹(如燕窝羹、鳝鱼羹、带子羹、凤果芥羹等),并没有专门的汤品。从烹饪方法来看,制作高级汤菜和羹的过程较为繁琐,通常会加入料酒、香油、蒜、火腿丝等各味调料,讲究的还要事先熬制上汤。如清末至民初广州有名的士绅江孔殷所创的“太史蛇羹”,在制作前便需专门用老鸡、瘦肉及火腿熬制并过滤出上汤。上汤对于羹和炖菜具有提鲜的重要作用,《美味求真》中收录的仅有两个“汤”,便是“吊上汤”和“熬素汤”两种上汤的做法。制作上汤其实与“煲老火汤”的方法有些相似,都通过熬煮“出味”。不过上汤通常并不加蔬果、药材等同煮,其实质只是烹制高级汤菜和羹的一道“辅料”。

而从清代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烹调习惯来看,“老火汤”则仍未具备流行的客观条件。一方面,老火汤需要耗费较多的肉类与燃料,成本较高。明清时期,虽然广东森林资源丰富,可提供大量的木材薪炭燃料,但随着矿冶、煮盐、烧窑、煮茧、制糖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燃料消耗急剧上升,供不应求的燃料导致柴薪价格持续攀升,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仅燃料一项就使老火汤难以成为普通人家的日常饮食。另一方面,大部分中下层阶级对于食材搭配以养生的意识较淡薄。以较早记述了广府中下层百姓日常煲汤情况的话本小说《俗话倾谈》为例。在故事《横纹柴》中,珊瑚见婆婆横纹柴受风失声,“即买防风、羌活、苏梗、薄荷,以驱风邪,又买党参扎者,以补元气”,食了两剂之后,横纹柴又要“买猪肉煲汤,以润肠肚”,话本中对驱风邪、补元气的汤剂均加以详细说明,讲到买猪肉煲汤时却并未提及其他材料,故猪肉极有可能是单独煮汤。加之横纹材在吃了猪肉汤后又“伤风夹腻,哑了喉咙”,可见其没有如今“对症煲汤”的意识。文中另一处对“煲猪骨汤”的描述亦与此相似。由此可推测,在日常生活中按性味搭配汤料煲汤以养生的饮食习惯在当时民间并不普遍。
从上文所分析的情况来看,至晚清时期,广东地区仍未形成煲老火汤的日常饮食习惯。对于普通阶层来说,熬制老火汤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过高,徐珂所说“餐必佐”的“汤”,多为制作简易、耗资较少的羹汤。而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他们更青睐于精致而古雅的羹,像老火汤这类只需将作料切块同煮的“粗放型”汤品,往往只能作为烹制高级汤菜的“辅料”。直至清末民初,随着工商阶层的崛起及广州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这种“尚羹轻汤”的饮食风尚才有所改变。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近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广州经济有了较为稳定的提升,酒楼数量也大为增加。与晚清时期酒楼多“上门到会”“会送”或“送席”的情况不同,日常堂食宴饮的需求增多。除了达官巨贾之外,一般的工商阶层、城市居民也成了许多酒楼招徕的主要客户。这些“新兴”的顾客群体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商人在酒楼茶室进行商业洽谈更是该时期的新风尚。他们对酒楼的环境与出品有所计较,但又不似达官巨贾不计成本地追求排场之奢华与馔食之精贵。因此,降低成本、创新菜式,是这时期许多酒楼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可以看到,“汤”在这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在酒楼餐饮业中,浓炖的“上汤”开始被改良并纳入食单,成为正式菜肴。随着粤菜的发展,“上汤”的地位愈发重要,除了羹和炖菜之外,一些高级菜馆的粤厨无论脍、炒、焖、泡都喜欢加上汤提味。上汤的熬制也有了一些改进,原先以武火熬制,再以鸡鸭血吸其浑浊油腻,难免带有血腥味;后改用慢火熬煮,则汤水清澈,最后再撇去油花即可。粤人对用上汤烹制的肉类汤菜十分偏好,在高级的筵席中几乎必不可少。然而以慢火熬上汤,汤渣弃之不用,再以汤水烹制精工细备的鱼肉诸菜,这类汤菜的制作成本着实不低。有食评家便指出,“请客之糜费,莫粤人若”。或是基于降低成本以迎合更广大顾客需求的考虑,一些酒楼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对原本只作为“辅料”的上汤作了改良,将汤熬至极浓,直接作为菜肴上桌。虽然对于讲究饮食的老饕而言,这个“上汤菜”饮汤尚可,熬煮过久的肉类却有些“不堪入口”。但是对于大部分顾客来说,既能喝到鲜美的上汤,又可吃肉,同时还减少了花费,何乐而不为?除了浓熬上汤以为菜之外,以盅出售的滋补养生炖品也开始在酒楼流行。但是大部分所谓的“原盅炖品”实际上并非以小盅隔水蒸炖,而是先用大瓦煲浓炖,再倒入炖盅里以图其美观罢了。这种大瓦煲浓炖的制作方式,与老火汤十分相似。

其次,在日常生活的饮食中,一些区别于简易羹汤、滚汤,口味更加浓郁、搭配更加丰富的汤品已经开始流行于普通的市民家庭中。除了节瓜汤、肉片芥菜汤等普通的滚汤之外,浓炖的瓜菜汤、肉汤也成为家常的待客菜式。在《广州民国日报》中写“食话”专栏的食评家朴以自己的家庭宴客菜单为例:大菜四簋,小菜四簋,因是夏季,则佐以浓炖的鲜陈鸭肾冬瓜汤。较之富豪人家宴客动辄三五十元,所费不过六、七元,却也精致可口,足以快意。另外,据陈梦因《食经》中所记,在民国后期,一些家庭已开始流行煲莲藕墨鱼猪肉汤之类的“礼拜汤”。
另外,从民国时期开始,人们煲汤越来越讲究食材搭配以养生。上文提到,晚清时普通人家大多没有按性味搭配汤料煲汤的习惯,如“煲猪肉汤”便常常只有猪肉一味。旧时粤港地区不少商店在给员工加菜时会煲“有味汤”,一般也是这种简单的“煲猪肉汤”。后有人提出,单以猪肉煲汤性寒伤胃且容易腻,可加猪粉肠同煲。陈梦因在写《食经》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讲究的方法,即除了猪肉、粉肠,再加上一些淮山、肇实、莲子、百合、红枣、陈皮一同煲约两小时半,既不伤胃,也不油腻。陈梦因所说的食方,与当下的老火汤已是十分类似,如汤料性味中和,讲究火候等。实际上,饮食性味相和、顺应节气等思想由来已久。岭南地区可入药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其药事活动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许多当地人很早便形成了辨别动植物性状性味的生活习惯,如东汉时期番禺人士杨孚所撰《异物志》中已有关于植物性味的描述。但要将这种养生思想普遍运用至日常食谱当中,一方面需要经济与时间条件的允许,另一方面则有赖于文化的传播。古代知识分子注重修身养生,精于医理者更著书以飨后人,如何其言撰《食物本草备考》。但对普通百姓而言,除非家中有体弱多病者,一般能深入接触这类知识的机会极少,更遑论时间与精力了。清末至民国初年,除了工商业发展带来生活水平提升之外,新闻报刊等大众传媒的兴起也是日常饮食养生意识提升的重要因素。如上文提及的陈梦因在《食经》中介绍如何煲猪肉汤可避免性寒伤胃,便是一例。
纵观清末至民国期间发展起来的“煲汤”,可以视作高级羹汤的“简化版”,也可以说是简易羹汤的“升级版”。无论是酒楼的“上汤菜”、大瓦煲炖的“原盅炖品”,还是家常的浓炖瓜菜肉汤,既通过浓炖的形式满足了粤人对“浓汤”的偏爱,又通过食材的搭配提升汤的养生价值,同时免去了制作高级汤菜或肉羹的繁复工序,大大节省了时间、精力与金钱。这个由“羹”到“汤”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由现代工商阶层崛起而带来的饮食风尚的转变。他们不似旧时精英分子偏好古雅,达官豪门追求奢华,又比农业社会时期的平民更加讲究口味与搭配,新闻报刊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也给他们带来了学习、交流饮食养生知识的平台,这便为煲汤与中医养生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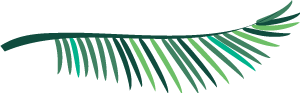
二、从“煲汤”到“老火汤”:
商业打造与饮食记忆对养生饮食的影响
从上文可知,至少在民国时期,广府地区日常饮食中已出现与老火汤相近的汤品,但“老火汤”却是晚近才出现的称呼。在访谈调查中,不少60-80岁的广州人表示,他们小时候并没有“老火汤”这一说法,而是直接称之为“煲汤”。那么,“老火汤”之名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其中有哪些因素在其中产生影响呢?
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生产力不足,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居民生活所需的粮肉、燃料大都凭证发放,物资十分有限,需要肉类、又讲究火候的“老火汤”在这时并不具备大范围流行的客观条件。不过,依旧有不少居民保持了煲汤的习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困难时期”,大部分家庭并无肉类可供煲汤,但在天热时偶尔也会煲一些瓜菜汤,平日则多是“菜滚菜”(滚菜汤)。7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略有提高,虽然肉类依然紧缺,但是居民煲汤的次数与样式明显有所增加。从调查情况来看,1950年代与1960年代生人普遍认同其青(少)年时期家里“间中”会煲汤,普通人家约一个月煲1-2次肉汤,平日则仍以瓜菜汤居多,且大多数会根据节气和应季食材煲相应的汤。据广州美食家、点心名师关伟强先生回忆,在他很小的时候(约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家里已时常煲汤,在不同的季节还会煲有不同功效的汤,如夏季祛湿,冬季温补,那时候市场还有配好的如“清补凉”之类的汤料出售。当时的汤并不及现在的老火汤丰富,汤料以广州及周边的土产为主,如节瓜、冬瓜、木棉、莲蓬、芡实、薏米等,珠三角盛产的河鱼也常常拿来煲汤,如“塘葛菜煲生鱼”就是一味养阴清热、健脾利水的家常靓汤。
20世纪80年代前后,率先试行改革开放的广东经济开始起飞,居民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改善,广式老火汤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发展成熟,并迅速流行起来。20世纪80-90年代可谓是老火汤“成名”的黄金时期,除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当中发挥了作用。

首先,中医食疗及药膳业的发展加强了居民饮食养生的观念。1980年代,随着生活的改善,人们在饮食方面开始讲究营养与健康。而在国际医学界,化学药物副作用对人体的危害逐渐引起关注,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对传统医学及非药物疗法的研究,基于中医食疗的传统,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提出着力发展中医营养学的构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中医食疗及药膳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一是药膳和保健食品行业蓬勃发展,如广州不仅有专营药膳的食肆,还设立了多家保健食品厂,成立“保健食品协会”,生产研发各类滋补营养食品、疗效食品和保健饮料。二是有不少关于家庭食疗的书籍陆续出版。1980年,广东中医学院的胡海天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梁剑辉医师合作,搜集、编写了《饮食疗法》,并于次年出版。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热烈欢迎,很快又出了“续一、续二、续三、续四”,1985年又以合集再版。与广州毗邻的香港、澳门,与家庭食疗相关的书籍也十分流行,如从1977至1984年期间,香港得利书局陆续出版了中医医师钟庸所著的《食疗药物》《中医中药》《民间医药》等著作,其中最受欢迎且很快再版重印的便是《食疗药物》。家庭食疗书籍的畅销,在侧面反映出人们对食品保健与养生的重视。当时家庭自制汤膳已十分普遍,尤其在冬令时节,不少药材店都会出售选配好的滋补汤料,种类丰富,有壮阳补肾、清润消燥、十全大补或驱风补气,各取所需,十分畅销,“包装两百多包,不到两天便售完”。
其次,商贸和餐饮业的发展推动了饮食创新,并直接引领了“老火汤”的流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旅游业与饮食业空前繁荣起来。由于地缘关系,不少港澳客商返粤开展投资合作,广州有不少在80年代改建或新开业的酒楼均是与港澳公司合资经营的,如大三元酒家、人人饭店、珠江海鲜酒家、大公酒楼等。港澳客商除了投入资金,参与酒店设计、经营以外,同时也从香港或澳门派遣厨师来粤,广东本地亦有不少厨师赴港澳考察。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广州及周边城市的饮食业受到了不少来自港澳的影响。从报刊及文史材料来看,“老火汤”这个名称正是在这个时期迅速流行起来的,并且极有可能与酒楼的推广有关。较早的如1987年在广州市环市东路花园酒店西侧开张的与港商合资经营的海鲜餐厅“南海渔村”,在最受欢迎的海鲜四人套餐中,第一道菜便是“渔村老火汤”。又如1984年在佛山开业的与澳商合资经营的旋宫酒店,开业几年陆续创制出百多款新菜式,其中“老火汤”便是其中最受欢迎的菜式之一,不少顾客认为其“清凉解热,清肝明目又润肺”。广州其他酒楼饭店也陆续推出各式精心创制的应季汤品,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老火汤”一词确切源于何处虽难以考究,其文化内涵却不言自明。“老火”曾用于中药方剂名,指文火慢煎以达到火候,如“老火葛水”。对于粤人来说,“老火汤”一词既点明汤水火候充足的特色,又使人自然联想到中医药膳养生之效,实在贴切,是以一经使用,便立刻流行起来。酒楼饭店为了招徕顾客,皆费尽心思推出招牌菜式,一方面要迎合当地人口味,二来还要突显新意。“老火汤”既满足了广东人对浓炖汤水的偏爱,又与当时注重食疗的趋势结合起来,自是大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酒楼还将老火汤与其他菜式以套餐的形式“打包”出售,并将老火汤列为首道菜式,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一种饮食习惯的形成。这是一种商业营销策略,也可能与港澳地区受西式套餐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第三,大量出版的汤谱,正式定义和诠释了“老火汤”,并为家庭烹饪提供了丰富而详细的参考指南。自酒楼不遗余力地创新、推广老火汤和炖汤以来,图书出版业继“食疗类”图书后,又将目光投向备受青睐的养生汤水。尤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汤相关的烹饪著作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在粤港澳地区大量涌现。这些汤谱一般由烹饪名家编撰,为家庭烹调提供了不同季节、不同养生功效的汤方。在这些烹饪类图书中,“老火汤”作为一类具有代表性的汤品正式被定义与解释,“煲三炖四”之类的“煲汤秘诀”也开始频频出现在这类书籍中。随着这些汤谱的出版和销售,老火汤的烹饪方式和理念对许多家庭日常饮食的影响也更加普遍和深入。
第四,随着商贸、旅游业等对外交流活动的扩大,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打造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趋势,“老火汤”也顺势成为广府文化的一张名片。以旅游业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介绍广东民俗文化的旅游地理类图书如观光指引、旅游导览等,开始将老火汤列为广州的特色美食之一。广东人素爱羹汤,但是推出具有广府文化特色的食物时,没有选择更早出现的羹、炖汤或滚汤,却选择了“后进”老火汤,或是因为前三者也常见于其他地区,难以突显特色。而老火汤以丰富的汤料熬足数个小时,味道鲜美,同时又四季变换,有养生之效,更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于是,在潜移默化之下,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外地人,通常提及广东的“煲汤”传统,言下之意便是指老火汤。
另外,除了这些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契机,老火汤在进入日常饮食的过程中,也逐渐内化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进而形成当地人的一种饮食记忆和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老火汤耗时较长、烹具容量大等烹饪特点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家庭日”常备饮食。这里的“家庭日”,是指家庭成员基本到齐,合家欢聚的时刻。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不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时间历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自民国元年(1911年)推行太阳历后,城镇工商各业多效行西方实施周休。在紧凑、繁忙的工作日之后,每周的休息日便成了放松和聚餐的时间。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工作日时大人必须上班,孩子需要上学,只有周末才是欢聚的“家庭日”。而从“老火汤”的烹调方式来看,既需要时间熬煨,又多用大的瓦煲,这样费时熬成的一大煲汤,自是最适合全家一齐享用。如上文提及的,在民国后期已有一些家庭开始有“煲礼拜汤”的习惯。在访谈中,也有不少退休老人表示,若只有一两人吃饭,将就做点紫菜汤、瘦肉水之类的滚汤即可,一般只有全家一起吃饭时才会煲汤。或是在晚上煲,如在药材公司退休的梁姨,她一般吃完早午茶或简单的午餐后去买菜,下午煲汤,煲好之后先熄火,等晚上“细佬仔”(对孩子的昵称)都回来,再开大火“滚一滚”、加盐调味就可以喝了;或是在周末煲,如在码头仓库退休的陈姨,她平均一周煲1-2次老火汤,都是在周末休息日,因为一家人都在,可以个个都“饮啖”(喝一口)。尤其在20世纪70-80年代,那时候生活刚刚开始好转,肉类依旧是十分珍贵的食材。许多访谈对象谈及这段时期,都会提到肉票的昂贵与紧缺:一张两毛五,平均每人每月限量4张。所以许多家庭一个月也就煲1-2次肉汤,主要是为了给老人和孩子补充营养。而煲汤这天就显得格外隆重,无论是在外工作或是读书,一旦收到母亲煲汤的通知,当晚必定齐齐回家吃饭,喝一碗“老妈靓汤”。
另一方面,烹饪对生活、生产模式的适应,间接强化了老火汤“浓郁”的烹饪特色。在调查中,我们发现,20世纪70-90年代前期是广东人煲汤平均时长最久的时期,不少人家煲3-4小时,有的甚至长达5-6小时,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老火”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源于物质匮乏时期形成的一种营养观念。尤其是经历过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代人,对他们来说,只有将所有汤料的“精华”全部熬出来,能够连骨带肉地吃完,才算是一煲“靓汤”。以工厂退休工人刘姨为例,她于80年代中期结婚,平时由家公(即公公)做饭,平均煲汤时间在3-4小时左右,若是煲西洋菜猪骨汤,则耗时更久,要煲到骨头变“绵”才算好。据刘姨回忆,她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坐月子期间,家公天天给她煲猪脚汤,几乎煲到“起胶”。

此外,“老火”的烹饪形式也是与生活、生产模式相互适应、协调的结果。在液化煤气大范围普及之前,城镇居民多使用煤炉烹饪。对于老火汤这类需要慢火熬煨的食物,煤炉具有实惠便捷的优势。在访谈中,不少受访者提到在20世纪70-90年代初,家中多使用煤炉煲汤,如果当天要上班,则可以在午休时间回家准备材料开始煲,下班回家再熄火。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安排煲汤的时间,无须看火,老火熬久一些也没关系,所以通常都会煲好几个小时。如曾在纺织厂工作的麦姨,她以前经常要上夜班,如果第二天要煲汤,则早上放工后去买菜,回家后先做家务,吃完午饭后开始煲汤,待汤滚开之后调小火,接着去睡觉,等傍晚睡醒,汤也就煲好了。此外,因为煤炉一般放在露天的地方使用,煲汤要慢火熬好几个小时,用的又是带孔隙的瓦煲,最后必然是香气四溢。在广州开旧书店的罗姨回忆起以前母亲煲汤,印象依然十分深刻:“老火汤很得意(有趣)的,因为你屋企(家里)一煲汤,(香气)就会飘出去两三公里,围着间屋(即街头巷尾)都会闻到,知道你哋(你们)今晚煲汤。煲几个钟那些汤真系(真是)很香!”结合上文,老火汤的香味与母亲的关爱及合家团聚的氛围融合产生通感,一想起来便会在心中泛起回忆与柔情,逐渐成为一种带着乡愁的、或是有母亲般温暖情怀的美好象征。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老火汤”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广府的日常生活、家庭的脉脉温情、母亲的殷殷关怀等,如著名的香港作家李碧华,其散文就多次提到老火汤。
综上,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药膳、商贸、餐饮、图书出版、旅游等多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形成合力,最终促使“煲汤”被重新命名、定义,并进一步打造成广东传统养生饮食“老火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发展、内化为广府人心中的文化情结。自此,广式老火汤的热度可谓是臻于全盛。

三、从“老火汤”重回“煲汤”:
传统养生观与现代营养学的碰撞
在20世纪90年代末,老火汤已成为许多广府人不可或缺的日常养生饮食,在这个时候却突然有了质疑之声。自1999年开始,不断有文章提出关于老火汤可能会“致癌”的说法,其依据主要来源于一个报道。报道称,1999年初美国芝加哥大学肿瘤学教授魏尔西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讲学时指出,过度加热食物会改变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性质,使其演变为致癌物质,如广州人喜爱的“老火汤”,数小时的熬煮不仅破坏了食物的维生素,也使得汤里有害物质的浓度越来越高。笔者几经查找,并未找到关于这次讲学的官方报道或研究论文,但是该说法却几经转载,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关于老火汤在健康养生方面的质疑开始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医学、营养学等专业领域也开始关注老火汤作为养生食品的价值及存在的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中西医营养学关于老火汤的养生功效存在争议。从现代医学、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虽然“老火汤致癌”一说没有事实依据,但从溶出成分及微量元素的分析来看,老火汤的营养价值不高,长时间熬煮以后对人体无益,长期食用还可能增加患病风险;而中医则认为老火汤吸收了千百年来传统食疗的经验,有助于改善身体状况,但需要正确熬制和食用。不过,大部分研究者认同老火汤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如过分熬煮导致嘌呤溢出,尿酸高、血脂高、肾病患者、肥胖人士等不宜多喝。
基于研究成果的发表及媒体的报道,如今有关“多喝老火汤不利于健康”的说法几乎家喻户晓。在笔者的调查访谈中,每一位受访者都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该信息。他们了解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新闻电台和书报杂志,如广州广播电视台的“健康100FUN”栏目,《健康报》《老人报》和《广州日报》等本地报刊,以及近年流行的微信公众号等;二是到医院看病或例行体检时,来自医生方面的建议;三是在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闲谈中得知。其中从第一、二种途径得知的人数最多,通常也最“有理有据”。大部分的受访者在谈及老火汤时,都能与“嘌呤”“尿酸”“痛风”等医学专业名词相联系。可见,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信息传播渠道的发展,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关于健康养生的知识与观念,以往可能多来源于长辈经验性的言传身教,如今则有更多的途径可以直接接收来自医生或专业机构的信息与建议。这些信息大部分是基于西方医学、营养学的研究方法,再根据实验数据量化分析取得,以现代的知识判断标准来看,是更加符合科学理性的。
按照西方营养学的建议,最佳的做法是摒弃老火汤,只喝营养成分保存得更好的滚汤。然而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广府人仍然保持煲汤的习惯,只是在频率和烹饪形式上作了调整。为了减少老火汤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人们可谓极尽所能地采取了各种办法。
一是减少煲汤次数,许多家庭从每天煲汤改为隔天或一周1-2次,其余时间则以滚汤代之。如在广州经商的李姨,因为前几年体检发现尿酸偏高,所以最近几年比较少煲老火汤了,但“仲系(还是)要煲,因为细佬(孩子)要饮”,只是从每天煲改为了一周2-3次,其余时间则改成菜心、枸杞、肉片之类的滚汤。二是减少煲汤时间,大部分家庭将煲汤时间由原来的2-4小时缩短至1-2小时。不过通常还要视食材而定,如甲鱼或部分根茎类药材(如五指毛桃、土茯苓等)则需要熬得久一些,果蔬瘦肉类则可能煲不到1小时。总体而言,如今已极少有人煲3个小时以上的老火汤。三是对食材进行处理或调整煲汤方式,以减少“嘌呤”溢出。食材方面,多选择脂肪较少的瘦肉,对肉类进行“飞水”处理,鸡先去皮再煲等等。在煲汤方式上,一些家庭选择用高压锅、焖烧锅来代替慢火熬汤,如参加舞蹈团的方姨,家中有老人痛风,但是因为孙子爱喝,所以仍然天天煲汤,但是不敢煲“老火”,一般先用压力锅煲18分钟左右压“出味”,再换到瓦煲里滚一下。再如在银行工作的陈姨,十几年前听说老火汤因沸腾太久而不利于健康,但家人都不爱喝滚汤,所以选择使用焖烧锅。一般先用瓦煲煲20分钟,然后放入焖烧锅中焗2-3小时,最后再换回瓦煲滚20分钟左右。使用高压锅、焖烧锅的家庭认为,这样既能避免汤水长时间沸腾,减少嘌呤溢出,同时又能“出味”。除了家庭烹饪之外,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则是当地人极少再在酒楼饭馆点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认为酒楼的老火汤很少飞水,食材也比较肥腻,虽然香浓,但可能不够健康。对当地人来说,除非遇到少见的汤式,平常还是自己在家煲汤更加放心。不过,酒席及大型围餐则仍以汤或羹开宴。

虽然从煲汤的次数和方式上看,老火汤的确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似乎宁可花费更多的精力减少“高嘌呤”问题,也要保持煲汤的饮食习惯。在调查中可以发现,广府人对煲汤的偏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味”,二是“啱饮”。“出味”是指通过熬煮使食材的味道融入水中。似乎从古代熬上汤制作汤菜开始,广东人就已对“出味”的浓汤尤为执着,即便如今为了减少嘌呤溢出而缩短煲汤时间,一般用瓦煲煲汤也不会短于40分钟,因为时间太短“出不了味”。一些家庭为了适应新的健康观念,近年来以果蔬煲汤,不再放肉,但仍坚持要煲“出味”。如曾任律师的傅姨,她们家已坚持煲素汤将近1年,每周一次,还是坚持用瓦煲煲足1个小时。“啱饮”则主要体现在按时令、气候及个人身体情况煲汤。如上文所说的傅姨,虽然在新的健康观念下改使用果蔬煲汤,但仍坚持“出味”和“啱饮”两个原则,汤料均按气候与家人的身体状况搭配选择,如“热”则用冬瓜、苦瓜搭配红萝卜和玉米,“湿”则加点薏米。又如在机关单位退休的蒙姨,她与丈夫血糖都偏高,不再煲“老火”的汤,但常煲有助于降血糖的番石榴瘦肉汤,用瓦煲煲45分钟左右即可。几乎每个访谈对象在谈及如何煲汤时,都能细数出不同节令、不同功效的汤方,这几乎成为了当地人的“本能”,正如陈梦因在《粤菜溯源录》中所评:“‘南蛮’食肆厨师、家庭主妇,好像精读《内经》,都懂得怎样为食客或家人‘荐其时食’”。
以上关于老火汤的变化与传承,还反映在人们对“老火汤”一词的态度上。笔者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对“老火汤”一词持模糊与暖昧的态度。一方面,谈及汤的种类时,将“老火汤”与“滚汤”对立,指出广东人更爱用瓦煲煲“出味”的老火汤,而不只是“三滚两滚”;另一方面,谈及健康养生的问题时,又将自己与“老火汤”划清界线,认为老火汤的确多喝无益,而自己煲汤的时间较短,不能算“老火”。人们对煲多久算“老火汤”的认知也各不相同,多数根据自身煲汤的情况来界定。如平时煲汤在3小时以内的,认为老火汤至少得煲3小时以上,而平时煲1个小时左右的,则认为1.5小时以上就可算是老火汤了。这种矛盾的结果,便是重回“煲汤”——人们似乎更适应和认同这个最初的称呼。
从老火汤的“被质疑”,到日常食用和烹饪方式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营养学对传统养生观念带来的显著影响。但正如人们对“老火汤”一词模棱两可的态度所隐喻的,他们否定“老火”,但依旧认同“煲汤”,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地人在这场由现代营养学与传统养生观碰撞所产生的“老火汤健康危机”中所采取的“自我调适”措施。一方面,接受现代营养学的忠告,调整煲汤的频率与方式,避免出现健康问题;另一方面,并不因此而放弃老火汤,选择现代营养学更加推崇的滚汤。因为对于当地人而言,“出味”和“啱饮”依旧是判断“靓汤”的标准。这种偏好与习惯由来已久,既受气候地理环境与传统医学思想长期的影响,又与现代各行业发展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模式相互适应,在文化上更是形成了一种认同感与向心力,因此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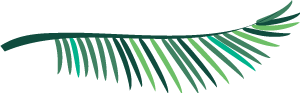
结 论
本文以广式老火汤为例,探讨一种日常养生饮食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总体来说,清末至民国期间,现代工商阶层崛起并引导了新的饮食需求,“煲汤”得以发展并替代“羹”成为新的饮食风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商业等发展的驱使下,“煲汤”开始被有意打造成广东传统养生食品“老火汤”,并在适应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进一步内化为当地人的饮食情结;进入21世纪之后,在现代医学、营养学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改变“老火汤”的烹饪方式,并倾向于使用对烹饪时间指向性更弱的初始称呼“煲汤”。
“羹-(煲)汤-老火汤”是老火汤由形成到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可以看到,老火汤基本的养生理念固然与岭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传统中医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在其进入日常饮食的过程中,其实受到更多来自商业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媒介、生产生活模式等多个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直接影响了广式老火汤在烹饪方式、名称、文化价值等各方面的变化。在以往关于老火汤文化的研究当中,大多数只注意到其烹饪特点与地理环境及中医思想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尽全面。例如,气候环境的影响只能说明羹汤类食物在岭南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若不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则难以解释为何“煲汤”这种饮食方式会取代“羹”在近代广东得到迅速发展,以及“老火汤”之名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后突然出现和流行;又如,煲老火汤要以文火慢熬,若仅用中医药膳的熬煮方式进行类比,则不免会忽略广府人对粤菜高汤的偏爱,以及使用煤炉对烹饪时间的影响等因素。可见,考察养生饮食的形成与变迁应当坚持整体论的研究方法,除了自然与医学理念,还要综合考察经济、文化、商业、科技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而从老火汤“重回”煲汤的过程,实际上则是传统养生观受到现代营养学冲击后,民众自我调整与选择的过程。现代医学已经通过实验数据证明老火汤存在不符合健康要求的因素,并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在广东人的日常饮食实践中,老火汤虽然经历了一些变革,但却未遭到摒弃,有些家庭甚至不惜花费更多的时间与金钱来“改进”煲汤的方法。“老火汤”依旧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商业发展的需要,还包括当地人世代相承的口味偏好、“阴阳五行”的文化认知模式以及作为家庭日饮食的文化象征意义等等,这些虽对关乎人类生存的营养保健、经济生产等物质实践要素并没有直接的作用,但却在维系家庭关系、处理人与自然间关系等方面具有难以取代的文化价值。可以看到,人们在饮食与养生的选择中,所依据的并不仅仅是科学评价体系下的“正确标准”,口味和文化意义也有重要的影响。
回到前言所提到的由于传统饮食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不适应性而导致的食物营养与健康问题。事实上,除了广式老火汤,世界各地还有不少传统饮食同样遭遇到了这样的“健康危机”。吕斯·贾尔(Luce Giard)在《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中提及现代人的饮食困境,人们在情感上常常倾向于符合童年口味、能够唤起文化记忆的传统饮食,但在由上而下推行的健康教育宣传机制之下,理智饮食似乎从来都是占上风的一面,最终便导致人们在传统习惯和现代饮食建议之间难以抉择。对于传统饮食习惯与现代营养学之间的冲突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广式老火汤的变迁研究中获得一些启示,应当以整体论的视角综合考虑人们的口味偏好、生活模式及文化需求等多种因素,而不仅仅将营养价值作为判断食物“优劣”的唯一标准。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拓展阅读
85.新青年 | 沈燕:灾害记忆何以传承——以一个村落地方神的变迁史为例
84.新青年 | 赖婷:心理学视角下的神话与神话主义——以罗洛·梅的《祈望神话》为中心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