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推介

王新艳,女,山东日照人。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日民俗学、海洋社会学。本文选取莱州市海神庙的重建为案例,剖析作为海神信仰空间载体的海神庙在重建后如何成为村落空间中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交汇的核心,又如何成为村民家族内部权力、本地村民与外地人、民众与基层组织或国家之间互动交流并实现村落群体认同的公共空间。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正是理解海神庙在社会的现代变迁中能够获得持续生命力并得以传承的内在原因。
公共空间与群体认同:
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探讨
——莱州市三山岛村海神庙的个案研究
王新艳
原文发表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03期
摘要: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各地庙宇纷纷重建。作为民间信仰活动的空间载体,海神庙的重建意味着村落公共空间的重塑。重塑后的公共空间成为村落空间中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交汇的核心,也成为村民家族内部权力、本地村民与外地人、民众与基层组织或国家之间互动交流并实现村落群体认同的公共空间。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正是理解海神庙在社会的现代变迁中能够获得持续生命力并得以传承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公共空间;群体认同;海神庙;寺庙重建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调整,民间信仰的生存环境也发生重要变化,其相关活动也逐渐复苏。表现之一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庙宇纷纷重建。庙宇作为民间信仰活动展开的重要场所之一,是民众信仰诉求表达的重要载体,其重建行为本身及其原因、意义作为研究对象自然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乡土传统可以在新时期特定的状况下,被民间加以改造,或恢复原来的意义,使之扮演新的角色。[1](p76)庙宇作为村落传统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新语境下如何被重新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就成为重要的问题。
期间,作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涉海实践中被创造出来的海神信仰,面对变化尤其迅猛的海洋实践,如何完成现代语境下的意义延伸?探讨海神信仰活动的场所与载体之一——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可以解释传统庙宇及其相关活动为何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中仍具有持续生命力并得以传承的内在动力。因此,本文选取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村的海神庙重建为研究对象,分析海神庙得以重建的原因及在当下的社会学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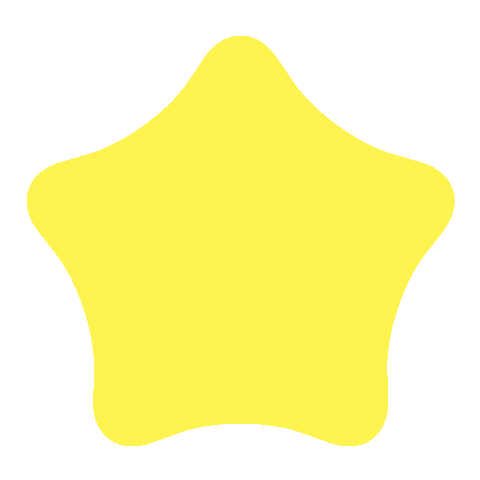
一 、三山岛村及其海神庙
莱州市三山岛村,位于莱州市区正北25公里处,毗邻渤海莱州湾。三面环海,因曾有三个山头耸立于海中,故名三山岛,于明清后逐渐与大陆相连。目前仅本地户籍的人口就有2123户,7000余人,外来务工人员约6000人,面积12.9平方公里,是胶东第一大自然村。明代,施、汪二姓氏从长江口崇明岛迁此立村,以鱼、农为生繁衍后代。时至今日,当地的渔业、农业、养殖业依然都很发达。而且,全国最大的海上金矿三山岛金矿就位于三山岛的北部海域。
三山岛水产资源极为丰富,盛产300余种海产品,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鲈鱼出口基地。目前三山岛村内用于远海捕捞的大型铁船就有312艘,用于近海捕捞或养殖的木船近500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莱州港就坐落在三山岛村辖区内,目前建成并投入营运的泊位共12个,其中10000吨级及以上泊位8个,50000吨级泊位4个,通过能力达到4000万吨。丰富的海产资源和运输能力使得三山岛村迅速发展,并于1983年在村落旧址保留的基础上,新扩建出今天的三山岛新村。

三山岛村海神庙也随着新村的落成,于1988年得以重建。重建后的海神庙坐落于三山岛新村的西北侧,座北朝南,八柱大殿,占地约56亩,供奉海神像、财神爷。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是三山岛村海神庙祭祀的日子。当天自凌晨开始,三山岛村及附近渔村的村民便陆陆续续自发来到神庙前燃香鸣鞭烧纸祭祀。为表示最大程度的虔诚,有信众凌晨0点,就会准时来到神庙前开始燃香叩首鸣鞭烧纸。上午8-11点是祭拜活动的高潮。正午过后,渐入尾声,仅有少数远途而来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的信众前来祭拜。整套祭拜过程结束,并不足20分钟,但往往祭拜完毕后,村民会在海神庙广场三五成群,交谈熙攘。不过尽管三山岛神庙祭祀仅持续1天,但前来参加祭拜的信众数量众多,根据2017年的粗略估计正月十三一天参加祭拜的信众就有两万人左右。因此,自2007年始,每逢正月十三,三山岛街道会派出部分警力前往海神庙维持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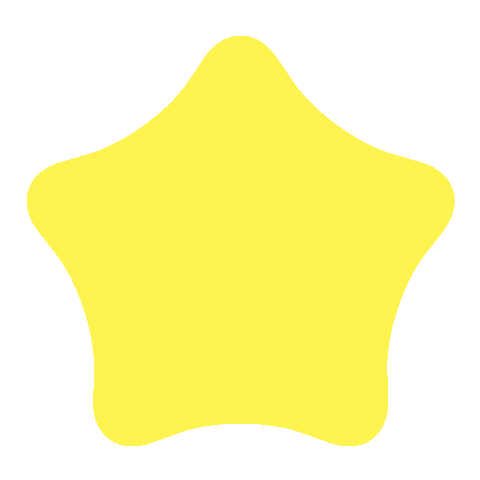
二、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力更迭:
三山岛海神庙建国后历次重建
(一)三山岛海神庙重建过程
关于三山岛海神庙的历史,并没有确凿的文献资料记载。据村民相传,世传八神山之一的阴主山就是三神山——现在的三山岛。但三山岛最初并不以海神信仰出名,而是道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今天在三山岛的中锋顶平坦处凿有盏石、九个酒樽、一双筷子和手掌印的印记,据说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冬巡寻仙等三山祭阴主的地方。而祭祀海神则直到明代施、汪两姓迁村至此后方才开始。因此在莱州有著名的东海神庙,以近两千年历史的皇家祭祀闻名。但三山岛海神庙供奉的却并非是东海神,而是泛泛而祭——所有海神。
建国后,在三山岛村旧址上一直有座简陋的石砌海神庙,内设海神排位,一盏香炉,仅此而已。文革期间,被迫拆除。农历正月十三的海神公开祭拜活动也几近中断。1983年三山岛村随着莱州港的落户,本地及外来务工人员迅速增加,渔业捕捞和渔业养殖也获得较大发展。因此经莱州市政府商讨决定在保留旧址的基础上,新扩建三山岛村。截至1991年,约百分之九十的原三山岛村的村民陆陆续续搬迁至新村。三山岛旧村除极少数村民由于年龄或养殖捕捞需要仍居住在此外,大部分房屋已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
因此,1987年三山岛村委会决定在新扩建的三山岛村重建海神庙,恢复农历正月十三在海神庙祭拜海神的活动。1988年由三山岛村村委会集体出资筹划、修建新的海神庙。新的海神庙落成后,海神庙祭拜活动也随之兴盛。与当时庙宇重建途径不同的是,三山岛村海神庙的重修决定、过程、费用等并没有采取村民募捐筹资的方式,而是由村集体全部包办。原因在于莱州港的落成、养殖业和捕捞业的大力发展,三山岛村集体的收入相当可观。

不过,自神庙重修后,近三十年来并没有进行定期维护,神庙管理人员也只有1人,且只在农历正月十三前后稍作收拾。因此,2014年海神庙再次塌陷,面临再次修葺的需要。关于如何修葺、谁来修葺,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三山岛村进行渔业专业合作社建设,成立了海麟、泓勃、海力、群胜、金鑫五个渔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曾有段时间群胜合作社欲牵头联合其他合作社共同出资修葺海神庙,后由于各合作社之间意见分歧,不了了之。另外,历来三山岛村的村委书记及村长一直以来由施、汪两姓竞争上岗。作为在村内实力相当的两大姓氏,每到换届选举前夕竞争的氛围尤其激烈。作为取得更多选票的资本之一,2017年现任村长决定自己出资重修坍塌的海神庙。当然,截至2017年底尚未开始动工。
根据加拿大籍汉学家卜正民提出的“寺庙重建”的分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类,拓展荒地完全新建一座寺庙;第二类重新竖立和建设曾经存在而今废弃的寺庙;第三类全面修复和扩大依然存在但破旧的寺庙;第四类小规模地修葺或装饰一直存在的寺庙。[2](p161)从1988年三山岛海神庙的重建可以看出,是拓展荒地重新建设曾经存在的寺庙,融合了第一类与第二类的方式。
(二)海神庙重建:村落公共空间的重塑与村落权力互动
根据曹海林对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的分类:一是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茶馆、宗祠、集市等;二是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如祭祀活动、红白喜事等[3]。根据曹海林的分类标准,很显然,海神庙祭拜属于三山岛村村落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海神庙便是村落公共空间的物质载体。其实关于公共空间的研究和论述可以追溯至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可以容纳公民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意见的场所。这种公共领域位于国家权威与私人领域之间,作为一种非官方的社会公共空间而存在。寺庙便是承载了传达和表现国家力量功能的空间载体,既非国家的,也非个人的。近现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精英作为联系国家与民众的桥梁时,很多时候便是利用了宗教力量和寺庙空间。因此,在梳理建国后三山岛海神庙的废除与重建中,就可以看到民众与基层自治组织、国家间的交流。
在全能型国家时期,国家力量的介入使得三山岛海神庙被拆除十余年,由于祭拜空间的消失,民间祭拜海神的活动和仪式也随之消退。直上直下的国家与民众关系彻底瓦解了社会公共空间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海神庙第一次重建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力量退场,由村委会直接投资包办。作为介于民众与政府力量之间的村委会,在寺庙重建中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受到国家对于民间信仰内在意义认可的影响,一方面来源于民众对于民间信仰和村落公共空间的内在诉求,二者缺一不可。国家与政府形式上的退场为海神庙的宗教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延伸腾出了空间。因此,重建后的三山岛海神庙自行发展为三山岛村民重要的公共空间。
在重建后的公共空间内,三山岛的民间信仰、民间传说的传统资源再次被挖掘出来,成为村落文化传递与重塑的桥梁。在访谈中,当地关于海神显灵的传说虽然无从考证,甚至与历史事实相左,但正是这些基于地方传统的传说构成了地方社会文化。并且杜赞奇认为地方传统总是可以根据当代需要加以重建或修饰的。这些经过修饰的地方信仰和民间传说通过海神庙的重建而得以传递和重塑。同时,在海神庙内人们交流的不仅仅是渔民对海神的祈愿,还包括信众之间的世俗生活的交流,包括民众对村落管理权力归属的态度和评价。比如2014年海神庙再次坍塌后,围绕海神庙的修葺,代表普通民众的渔业合作社的出场,代表村落政治权利的村长的出资,都在这个公共空间内得以呈现。神圣性与世俗性同在的特殊公共空间的属性,进一步增强了海神庙不断得以重建的内在价值。

伴随着海神庙的重建,农历正月十三的海神庙祭拜活动也得到复兴。参加祭拜的人数逐年增多,从三山岛村民逐渐扩大至三山岛的外来务工人员、相邻渔村的渔民等;祭拜仪式也越来越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燃香鸣鞭烧纸,供品种类的丰富、捐款祈福、秧歌等民间表演等活动也逐渐加入进来。“仪式活动的增加可能是实用的、个人主义的策略,新起的一代要借此适应正在兴起中的市场经济”[4](p78)因此,海神庙祭拜对于三山岛居民来说不仅有民间宗教意义,更多得包含了地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信息,承载和传递着地方文化。这使得重建后的海神庙空间处于村落空间中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的核心空间位置。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原有的村落中的机械团结逐渐削弱,分工合作的有机团结逐渐增强,人口流动也愈加频繁。面对原有维持村落团结的传统资源的凋零、群体聚集场合的不断减少,海神庙的现代重建作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空间,以及其内部发生互动的多样性,共同促使重建后的海神庙成为当地村民心理慰藉的场所,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信仰、娱乐、心理等需求的满足。相对固定的人群在固定的场域、固定的时间进行定期性的交流。村落的世俗生活、经济、宗教以及地方文化也借助海神庙庙空间向四周辐射延伸。同时还地承载了国家、民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承担了地方文化重塑和传承的功能。
综上,重建的海神庙作为地方文化与民间信仰传承的空间,体现了村落公共空间的重塑过程。在这层空间中,既具有作为村落公共空间寻求群体共同交流形成共同心理机制的作用,也包括了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地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传承。同时,在其重建过程中,折射出了国家与民众间的交流与沟通。
将重建海神庙视为村落公共空间的重塑来探讨,不仅囿于宗教意义上的寺庙,将会拓展其在国家与民众、神圣与世俗、传统与现代、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意义和研究的理论领域,使其内涵更加丰富。
在此基础上,接下来从公共空间重塑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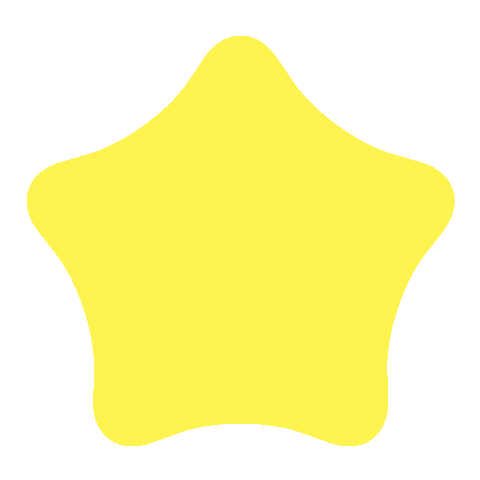
三、群体认同: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
近些年来对于庙宇重建的研究很多。骆建建《归来之神:一个乡村寺庙重建的民族志考察》一文中,按照不同学科将庙宇重建的研究分为了如下四类:第一类,从政治意识形态上,秉承“无神论”的立场,批判寺庙重建中“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第二类,从宗教学角度,着重描述寺庙重建风潮下宗教信仰的状况;第三类,从经济学层面出发,将寺庙重建视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一种实践,将其视为开发寺庙、发展旅游的经济策略;第四类,主要关注寺庙重建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变迁,探讨寺庙与社区记忆、文化资本、地方传统、国家权力的关系[5]。但目前的研究无论从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庙宇重建,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庙宇重建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意义,而没有继续探讨庙宇重建后带来的后续影响。通过上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庙宇在村落空间中处于核心位置,其承担内容和作为公共空间承担功能的多样性、民众对于民间信仰的诉求决定了其被重建的必然性。但重建后之所以能够被村落居民持续利用,且日渐兴盛,其原因更多在于海神庙在现代的村落社会生活中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下面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来分析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
微观层面,通过海神庙祭拜,完成了家庭内部权力的代际传递,并将家庭内部的权力变化通过这一公共空间中向村落其他成员传达,以期获得村落成员的认可。在调查中随机抽取的50人中,有39人年龄在28-55岁,已婚,占78%。另有4人在26-30岁,已婚。有7人在56岁以上,儿女均不在三山岛村,其中有4人的儿女尚未结婚。据当地人解释,三山岛海神庙祭拜有条默认的规矩:如果儿子已经结婚成家,则父母亲将会从祭拜主体中退出,由已婚的儿子代表家庭进行祭拜,当地人称由“当家的”去祭拜海神庙。由此可见,在海神庙这一个村落公共空间中,祭拜人代表的是整个子家庭和母家庭在内的家族,宣示的是子母家庭主权的归属。每年三山岛海神庙祭拜都会出现一些新鲜的年轻面孔,这往往是当年或近几年结婚的年轻人,看到在海神庙祭拜出现的家庭成员发生变化后,村落事务或家庭之间的互动主角也会随之出现变化。因此,如果说婚礼是婚姻获得社区或村落共同体认同两人婚姻合“法”性的传统习俗性仪式的话,在三山岛村,海神庙祭祀则是某一家庭成员主权正式确立并获得村落共同体集体认同的标志。
当然在特定情况下,会发生反复。比如调查中有一位汪某,今年(2017年)61岁。2014年儿子结婚,婚前一直在烟台市区打工。2014年结婚后在家与父亲共同经营一艘远海捕捞船。2015年的海神庙祭拜就由其儿子前去燃香鸣鞭烧纸供奉。2016年汪某的儿子以经营渔船辛苦为由,春节刚过便与妻子再次外出务工,海神庙祭拜再次回归到61岁汪某身上。不过,汪某解释说“只要儿子回来,正月十三还是得由他去海神庙”。可见,海神庙作为三山岛村的公共空间,其祭拜规则的约束力首先局限于在三山岛内进行生产生活的群体内部。
中观上,通过是否参与正月十三海神庙祭拜,三山岛居民将本地人与外地人(他者)区别开来。作为胶东经济较为发达的重要渔村之一,与其它沿海发达渔村一样,近年来三山岛村的外来务工人员人数众多,三山岛村外来务工人员在数量上几乎与本地人口相同,据2017年村委会的不完全统计,本村户籍人口7000余人,外来务工人员约6000人。甚至在2015年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曾一度超过三山岛村的原住民。由于三山岛村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历史较长,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陆续有来自河南、四川、东北等地的青壮劳动力前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此结婚、成家或将家人接到三山岛村的“外地人”比例也越来越高。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并获得当地人的认同,是每一个意愿留在三山岛村生活的外地人努力的方向。这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农村民间祭祀中很少遇见的社会现象。一则在现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仍然没有发展成为高收益、高产出的产业,外地人口流入的动力不足;二则现代农业社会的民间祭祀活动几乎被打散在日常生活有所求之时或特定的时令节气中,且民间祭祀的区域性和组织性特征较渔村较弱。

在村落的文化逻辑中,来自他者的群体认同对于自我认同而言,更能确定和强化自己的身份。因此,外来务工人员能否被以“当地人”对待,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自己是否认为已经融入村落的生产生活,更重要的是三山岛本地村民的态度和认同。在访谈中,“在此结婚”、“购房”、“居住10年以上”、“祭拜海神庙”是被三山岛村民认为从“外地人”转变为“当地人”的四个必要条件,而在外来务工人员的自我认同中,并没有提到“祭拜海神庙”一项。可见,能否“祭拜海神庙”在当地人的认同逻辑中是一项重要的心理归属象征。这也是民间信仰的重要作用之一。因此,祭拜海神庙可以看作是“外地人”获得他者的群体认同的标志性事件,海神庙重建正是为标志性事件的发生的提供了空间和物质载体。通过共同参与祭拜海神庙,“当地人”与“外地人”在海神庙内迅速消除界限,实现了本地居民对外地居民的群体认同。
从宏观上看,海神庙的重建还体现了民众对基层政府及村落权力归属的群体认同。海神庙作为公共空间的场域,其重建不只在于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因素的考量,更多的涉及社会结构的转变,村民价值观念和行为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海神庙的重建并不仅在于民间信仰的简单复兴,而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与村落公共空间的塑造。而海神庙的重建主体也折射出民众与基层政府、国家之间的互动、博弈和交流。2014年海神庙坍塌以后,正遇上三山岛村渔业合作社建设,民众对其接受程度和情感认同并不成熟,因此虽多次商讨仍然无果。这从侧面反映出2015年前后,三山岛村的渔业合作社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民众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在号召海神庙修葺过程中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发挥作用。同样,2017年三山岛村委选举前夕,在任的村长将出资修葺海神庙作为再次当选的筹码之一,也是深刻认识到海神庙在村民心中的位置,希望通过修葺行为获得村民的群体认同,放心将村落管理权交由自己。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是次要的。村落社会的联系分工呈现出机械团结的特质,村落里的个人同化为具有共同信仰和情感认同的整体,这种团结以牺牲个性为代价,通过周期性的集体宗教仪式将其机械团结在一起,所谓集体宗教仪式在近现代便体现在年度的祭祀活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力量从民间社会的形式性淡出后,村民个人与集体的互动被突出出来。1988年海神庙的重建以及2014年再次坍塌后面临的修葺讨论,国家仅以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参与到民间活动中,重建的过程既凸显了国家的权威,同时也为民间力量的能动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因此,重建海神庙其实是现代渔村面临家族结构变化、渔村人口流动频繁、村落利益竞争与冲突的社会结构变迁中,为寻求和重新构建群体认同找到一个出口。通过海神庙的重建和海神庙祭拜活动的复兴,家庭主权的更新换代在其过程中获得村落共同体的群体认同,“他者”获得本地人的群体认同,国家权威和村落基层组织的权力获得民众的群体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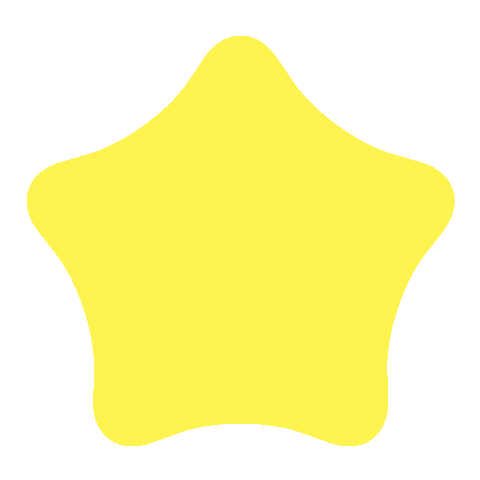
四、结论
面对国家提出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吁和要求,各地政府纷纷将地方传统文化视为一种文化的、社会的资源,积极参与其挖掘、开发、利用和保护中,以避免更多优秀传统文化走向衰微。但国家力量的干预超过一定度后,也会带来诸如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文化内涵的过度解释、商业化操作意味远远超过文化价值等负面效果。其实,除却将传统文化视为资源的传承保护路径之外,传统文化自身在现代社会适应中也表现出强劲的内在生命力。
三山岛海神庙的重建和海神祭拜活动的复兴,恰恰展现出了传统民间信仰在现代语境下的意义延伸,作为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重建后的海神庙成为村落公共空间的核心,在其中,村落内的家庭代际变化、村落本地人与外地人、村落民众与基层自治组织及国家权力完成了互动和交流,在互动与交流过程中通过集体性的海神庙祭拜活动完成了群体认同。同时,这种集体性的祭拜又是三山岛民众自发组织和进行的,体现出民间信仰意义被削弱、社会学意义得到加强后的传统民间信仰的内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将会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寻找到另外一条路径和思路。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拓展阅读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