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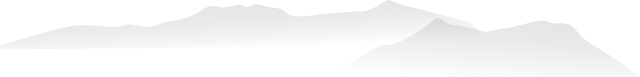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罗士泂,男,江西泰和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乡村社会研究、社会史研究、物的人类学研究。本文尝试从微观层面出发,细数一个名为“查二妙堂”的墨店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诸多困扰,具体而言将会从家族内部成员的利益争夺、其他墨号的仿冒、深陷上海墨匠罢工风潮三点展开。以此为基础窥视整个墨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纠纷问题并反思墨业的发展。
物的社会生命:徽墨的社会史研究
——基于个案的历史分析
罗士泂
原文发表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摘要:清末民初的墨业市场中,无论是家族内部成员还是其他墨店的人员都会通过盗用、仿冒等方式从事伪墨的生产,墨店主人应对此类纷争的方式不一而足:或登报刊载声明,或注册商标,或请求官方介入进行裁决。此外,墨工与墨店之间的关系也在西方近代工商业的冲击之下变得紧张起来甚至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事件。在诸多内外力的作用之下,中国传统墨业逐渐式微。
关键词:徽墨;纠纷;物的社会生命
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墨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进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大通商口岸的开放,大量被称之为“洋货”的产品进入中国这广阔的地域之中,这其中包括外来市场的墨汁、铅笔、钢笔等新式书写工具。这些产品的进入对于墨业的发展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乃至发展到这一局面:墨在中国传统书写工具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被取代,中国传统墨业从此逐渐衰落下去。在此背景之下,通过关注某一墨店或墨号的整体运行状况并以此来窥视整个墨业的发展态势遂成为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径。本文尝试从微观层面出发,细数一个名为“查二妙堂”的墨店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诸多困扰,具体而言将会从家族内部成员的利益争夺、其他墨号的仿冒、深陷上海墨匠罢工风潮三点展开。以此为基础窥视整个墨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纠纷问题并反思墨业的发展。

周绍良通过“查二妙堂墨”、“查二妙堂绍记墨”、“查二妙堂友记修竹斋墨”这几笏墨的相关记载,对于查二妙堂发展历史有过相关推断,兹将其主要意思复述于此:查二妙堂为道光初年新兴之墨肆,事业相当发达,至少工艺可与胡学文、潘逢吉相伯仲。但至同治年间,突有巨变,墨肆重新改组,不知是有人参股抑系墨肆易主?从实物上体现,店名之下增加“绍记”字样,说明查二妙堂不再是当日原班人马。内容情况若何,于今无复资料说明之,但事实不再是查二妙堂,而是二妙堂绍记。大约在光绪某年,二妙堂重又改组,由绍记改作“友记”,号“友于氏”,至此“二妙堂”已三世矣。按墨肆习惯,多以店主姓名,其招牌何称,始终未见有实物标之者。晚清之际,改加“绍记”,继而又改加“友记”,常标有“友于氏”款识,始发现有用“修竹斋”之店名招牌,不知其原有,抑后来补加?均无资料说明之。[1]换言之,周氏认为查二妙堂经历了“查二妙堂”、“查二妙堂绍记”、“查二妙堂友记”三个阶段,并且三者之间乃接替进行。对于这种说法,部分内容实则需要修正。

根据《从农商部公司注册观察中国化学工业之现状》这一份资料显示:查二妙堂绍记香墨厂,制旧笔墨,资本五万元,在上海小东门内大街,设于咸丰年间,民国三年五月注册。 [2]可以看到,查二妙堂绍记最初是设于咸丰年间,而非周氏所说的“同治年间”。它所显示的注册时间是在1914年5月,而查二妙堂友记甚至在1910年之时便提出了注册申请。有资料显示,1910年2月清政府在执行商法之时,曾批示镇江商务分会:
商人查济□、查济柄、查济纯三人合资开设查二妙堂友于氏友记墨号,援合资有限公司之例,呈请注册。查公司律第五条内载,合资公司所办各事,应公举出资者一人或二人经理,以专责成。又第七条内载,设立合资有限公司,集资个人应立合同,联名签押,载明作何贸易,每人出资若干,某年某月某日起期限以几年为度,报部注册等语。本部详阅该号原呈,所开经理人查益生,并非出资之人,于有限无限一款漏未填写,合资合同亦未呈送到部。以上各节均与定章不符,合行批示该商会仰即饬该商等遵照定章抄录合同另具呈式,公举经理人报部查核。[3]
当时查氏三人准备合资开设查二妙堂友于氏友记墨号,因为不符规定而被要求重新补充完善相关资料。不过,查益生最终仍如愿担任了该墨号的经理。如王振忠在研究上海的徽商之时,曾谈论徽宁思恭堂征信录时,介绍的“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止婺邑长生愿捐数芳名”,捐款便是由“查二妙堂友记益生经手”。[4]而在1920年公布的《上海商业名录∙民国九年》中我们也能看到经理就是查益生。[5]由此可见,在1910年提出申请被驳回后,查二妙堂友记必然根据相关要求又再次提出了申请。
此外,资料显示,绍记并没有被友记所取代,相反两者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因为迟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仍有资料记载上海南市一批名店迁入租界,其中查二妙堂绍记墨庄便是迁入广东路240号。[6]而在1924年《工程处报告十三年十二月份发给各项营造执照》中我们所能见到的记载仍是查二妙堂,而非其他名称,[7]另外,根据上海地区商号的信息记载,查二妙堂友记与查二妙堂曾并存于上海的小东门内方浜路,只是前者的店铺门牌号是86号,后者是40号而已。[8]因此,所谓的查二妙堂被绍记取代的说法无法站住脚。综合看来,周氏的推断的确如其所言,仍存有很多困惑之处,需要有更多资料才能完整捋顺查二妙堂的发展历程。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查二妙堂墨号自道光初年创立之后便遭遇了多方面的纠纷困扰。本部分将分而述之。
(一)家族内部成员的利益争夺
关于查二妙堂墨号的家族内部纠纷问题,主要刊载于《申报》之中。事端起源于查二妙堂墨庄主人查人基的堂弟及其堂弟的母亲来到上海,“冀分余润”。详见此则信息:
邑庙东首有查二妙堂墨庄,主人乃歙人查人基也。日前忽有堂弟西龄偕母自歙来申,欲分贏余银两。人基以弟曾出继与陈姓,既已谓他人父,岂容夺我貲財。前日将西龄扭至上海县署,以盘踞滋扰等词喊控。王司马饬将西龄父差看管,着人基开呈节略候讯。[9]
这个名为陈西龄的人虽然曾是查二妙堂墨庄主人的堂弟,但是由于已经过继给陈姓家族,因此企图分得墨庄利润的愿望被查人基断然拒绝,并被查人基以“盘踞滋扰”作为控告理由送至官府。三天之后,《申报》再次刊载了该纷争的详细消息。
本城查二妙堂墨庄主查人基,扭控陈西龄盘踞滋扰等情,曾登前报。前晚王司马庭訉之下,查诉称:西龄虽是堂弟,然已为姑母陈姓螟蛉,今忽偕母来申盘踞滋扰。西龄供称:二妙堂系祖父创开,小的与人基系同祖昆季,理应分润。伊竟据为己有,实属天理不容。司马饬两造邀同亲戚来案覆讯核办查。又诉称:伊母现在店中吵闹,叩求驱逐。司马俯准所求,饬令差传谕该氏毋许吵闹,如违提究查。乃叩谢而退。[10]

此处得知更为具体的信息:陈西龄的母亲同时还是查人基的姑母。也就是说两家实际上有着较为紧密的亲戚关系。即便如此,由于她在墨店中吵闹,因此查人基请求将其“驱逐”出店。而官府原则上批准了该请求,并饬令其姑母,一旦她再吵闹将会被“究查”。也许是该母子二人“盘踞”时间太长,几天之后,查人基再次请求将二人“递解回籍”。
查二妙堂墨庄主查人基,扭控堂弟西龄盘踞滋扰。帮审委員王雁臣司马,谕令邀同亲族覆讯等情前已叠登于报。前晚司马升堂覆讯,人基诉称原籍婺源县,叩求递解回籍。司马俯准所请,饬将两造一并递回。西龄一再叩求,称母亲年老在路不便。司马乃饬将西龄交人保出各自同籍投县伸理,两造返遵谕而退。[11]
事情最终算是告下一段落,两人被遣返回原籍所在地——婺源。
上述案例的信息很清楚地指明此次争论的焦点在于陈西龄的“身份”以及身份背后所牵涉的利益纠葛问题。在清代,“遗产之继承,惟限于直系卑属之男子,盖以宗祧继承为前提也,因之无子者必立嗣子”。[12]也就是说,“一个男子必须从宗祧祭祀和财产两个方面被其子所继承。如果他没有亲生子嗣,那么他必须过继一个嗣子来延续父系家庭以继续对祖先的祭祀。人们一般认为,承祧与分家互为表里,它们是同一事物——即只有儿子有承继权的两个侧面。”[13]陈西龄所提出的“分贏余银两”的依据就在于他与查人基源于同一个祖先,从他提出要求的逻辑来看,他自然认为这足以成为分享祖先遗留下来的家产乃至依托这份家产创造出来的财富的现实依据。但是,对于陈西龄已经从查氏家族过继至陈姓家族从而接续后者血脉这一事实而言,他要想从查氏家族中获得任何的财产分配无疑是不可能。相反,由于他已经获得了陈姓家族成员的“身份”,并且这种身份为他提供了陈姓家族的宗祧祭祀和财产继承的所有理由。要知道,清代在处理财产分割之时秉持的大原则是财产始终应该保留在同族之手(即在广义上的家的内部)。[14]即便陈西龄身上流淌着查姓血液,乃至陈西龄的母亲与查人基还存在姑侄关系,但是查人基不可能再将他视为查姓家族的一员,对于他所提出的利润分割的要求不予答应也就得到了理解。
此外,查二妙堂友于氏还曾遭遇宗族内部成员仿冒墨牌从事生产、销售等可能有损自身商业利益的行径。此份声明便是此类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纠葛的一个典型案例。
声明查颂修假冒二妙堂墨牌
僕等承租遗开设,查二妙堂墨店于沪城,以及各处分店。经历六十余年,宣统元年族棍查颂修,苏垣假冒小号牌名,私造伪墨经。小号控奉吴县提究查颂修,情虚畏讯鬿捲零货逃匿,美租借海宁路馥康里,又复设作欺骗商人,又经小号叠控□农工商部江督沪道,均批公廨查禁在案。现正□公堂饬保带,旧历上年腊月十三日,新闻报载:在海宁路馥康里二妙堂失火一则阅之,不胜诧异。查颂修假冒小号二妙堂牌名,已奉各大批饬,查明吴县案卷。究禁查颂修,自应改悔前非。尤敢在外招摇希图鱼目,实属无耻。已极小号为名誉起见,诚恐泾渭不分,为此登报声明扶惟,公鉴。
查二妙堂墨店友绍记主人查济镄、查济杰谨白
查二妙堂墨店的两位主人将“查颂修”称之为“族棍”,便表明了双方同属于一个家族/宗族这层关系。查颂修最初因为假冒查二妙堂墨店的牌名,被控告至官府,随后因为“情虚畏讯”而逃亡他处。未曾想,之后又在租界之中“重操旧业”。查二妙堂墨店的主人发现这一情况之后,为了避免消费者被蒙蔽,遂采用这种“登报”的方式予以告知。

(二)友干氏:友于氏的“山寨版”
不仅家族内部成员会盗用牌名,其他姓氏的人员同样也会盗用查二妙堂的牌名。首先来看一份名为《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在人候补道松江府上海县正堂田》 的告示:
为给示晓谕,事据监生查济杰禀称:先祖友于氏于道光丙午年在治下小东门内开设查二妙堂笔墨牌号有年,缘以先祖字友于、号绍成,凡制品上品香墨其板均刻友于氏绍记字样,□宗谱可证,经令六十余年,名驰中外。前有不孝之徒以友干氏假冒友于氏牌号暗地销售,近又有无耻之辈仍敢以伪乱真,不无与二妙堂友于氏绍记牌号大有妨碍。伏查古人云,凡笃友未闻笃友干,显系杜撰,鱼目混珠,其潜施鬼蜮不言而喻。求情给示晓谕以杜假冒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给示晓谕。为此示仰墨业诸色人等一体知悉。须知友于氏绍记创此牌号货真价实,所以买客信用自示,以后务各守分安业,勿再假冒牌号布图渔利。其各凛遵母违特示。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示
查二妙堂“友于氏”墨牌号被“友干氏”所冒用,并被后者用来从事暗地生产与销售,此举自然遭到友于氏方面的极为不满,因而被“监生”查济杰告知到上海县正堂处,遂出现此份官府告示。可以看出,这是友于氏墨号企图通过官府告示,用以确证自身墨号不可侵犯的合法性地位的一种努力。当然这只能算是“打假”方式的一种,毕竟告示所持续的时间有限,并且影响的范围不见得能够覆盖到该县其他地域之外。查二妙所生产的墨品全部销于国内,[15]为保证其正当利益,因此在墨票上乃至于直接在注册商标之时都将这一份“声明”贴出,更显示其捍卫自身商业利益的决心。
而这一假冒现象发生的时间甚至可追溯至光绪十二年(1886),来自光绪年间的一份声明更是被友于氏在民国十二年(1923)申请商标之时一并呈递上去。《查二妙堂友于氏商标注册证》[16]这份资料显示查二妙堂友于氏在民国十二年之时呈请注册商标,并于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一日正式登记注册:
中华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注册给证
专用期限 自十六年九月十一日起至三十六年九月十日止
商标名称 友于氏
专用商品 第五十类 徽墨
国籍或省区别 江苏省
商号及呈请人 查二妙堂墨号查济纯、查济钱
在上海城隍庙东大街六十八号
注册商标 第一二五三四号 审定书第五九()号
呈请号数 十二年收文第九零七号
呈请年月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日
从本质上来说,注册商标便是宣示其墨号的专有性。然而在注册给证的信息之上,同时还有一份来自于光绪年间二妙堂主人所发表的声明。详文如下:
本堂提选细烟精制香墨不惜工料,创始于道光丙午迄今名驰中外四十余年。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近又无耻之徒伪造本堂友于氏牌号,又有不良之辈取友干氏,干于相似,假货乱真,渔利欺人,害人不浅。今特加以内仿帖以辨真伪,如蒙正派好庶不致悮。
光绪十二年岁在丙戌冬月二妙堂主人谨白
为打击盗用其名的“友干氏”,他们甚至将这么一份声明放置于注册商标之上,这在其他同类注册的商标上是不曾见到的现象。换言之,直接将一份声明放入商标之中客观上也能反映友于氏墨号为打击伪造假冒的墨牌花费了较大的精力,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实则在更大范围内宣告自身的独有性。当然,这种行径也恰恰反映出此类伪造难于纠正及管理的困境。友干氏冒用友于氏的牌号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这种行径所反映的一个问题是,墨牌号品牌自身价值的重要性。此处我们缺乏更多有关友于氏与友干氏之间的详细案例信息,但是,此类纠纷伴随着查二妙堂墨的发展并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
正如范金民所言:“围绕着假冒字号商标发生的纠纷以及随之而来的诉讼,构成了清代商业诉讼的重要内容。”[17]对此,黎志刚、韩格理也曾如此说道:“商标假冒是近世中国流行的一种商业现象。”当然他们同时也表示,“中国的地方政府、商业性行会、家族及商人均尽力保障商标的专利权。”[18]从该案例的相关信息可得知,该墨号在遭遇权利侵害之后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来应对。一是通过官府的呈控,要求官府出示谕禁,而这也是当时商人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的重要举措。[17]为维护字号的信誉和市场的秩序,官府总是站在被侵权或实际受害者的一边,通过赔偿损失、勒令禁止假冒、要求字号具结保证、立碑周示等措施和方式,维护字号的合法权益。[17]安守廉对于官府的此类行为,曾如此评价:“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行会保护商号或商标,真正的用意是通过维护商业秩序、减少民众的欺诈事件以保持社会和谐,这种解读绝非标新立异。”[19]
从案例中的告示可以得知,在查二妙堂墨号向官府呈控之后,当地官府也的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然而,这一方式并没有在多大范围内奏效,至少我们可以看见查二妙堂墨号采取了第二个措施来防止和杜绝这种假冒现象,即通过商标注册等方式完善自己的商标标识。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正经历一场“枪口逼迫下的法律启蒙”[19],一种被称之为西方知识产权的观念由此输入到中国。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细目》。该章程规定无论华商、洋商欲专用商标的都须依章程注册,并对商标申请及其优先权、商标不得注册事由、商标审查、侵害商标专用权及其处理办法、侵害商标专用权犯罪等做了规定。1923年,农商部商标局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商标公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全国注册局,专业办理商标等注册事项。[20]友于氏商标正是在注册局成立当年便申请注册。此类规章制度的颁布,也为诸多的商业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从上述案例中可以发现,友于氏墨牌号为了杜绝友干氏的假冒现象大费周折,各类严正声明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此类商标法正式在中国开始实施之后,显然为它提供了又一个渠道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三)陷入墨匠罢工风潮
据统计,在1918——1936年这十几年间,上海地区的罢工次数高达1504次,[21]其次数之高让人不得不惊叹当时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而相较于当时的纺织、造纸、印刷等工厂来说,墨店数量以及工人数量自然无法与之匹敌,“全沪笔作场共三十九家,墨作场二十六家”[22]。具体到一个墨店的人员构成,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前店后厂”。前店主要是由经理、账房、跑街、柜台等职员组成;后厂则主要由经理及制墨工人组成,工人主要从事和料、做坯、洗水、削边、磨边、誊字等工作。[23]也就是说,一个规模较大的墨店的人数一般也就维持在几十人左右。相较而言,墨匠罢工的次数以及人数都很少,不过根据刘石吉对于1924年上海徽帮墨匠的这次罢工风潮的详细研究,我们能了解到此次罢工不仅牵涉到墨工400余人,持续时间更是长达两个月左右。查二妙堂便陷于此次风潮之中。
1924年5月31日,“以绩溪、歙县两郡墨工胡洪炳、许炳炎、朱良臣、汪钜铎等,以及婺源墨工朱润斌、程炜庭、王利丰、俞金桂、余包杰等为首”的徽帮墨工,[24]以生计维艰为由,向店主二妙堂等数十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数量,由此拉开了此次罢工风潮的序幕。在墨店与墨工对峙期间,徽宁同乡会评议婺源人俞郎溪,曾独自前往墨业大店查二妙、詹大有(此次罢工风潮中态度最为强硬的一派)处调解,然而他们却仍然坚持不妥协。即便经工会与墨工代表接洽,再三向查二妙、詹大有等作主劝商让步,仍没有结果。直至7月25日墨工方面得知多数店主对于中秋日开始加薪,此次罢工才得以告一段落。[25]
外界对于此次罢工众说纷纭。撇去那些直接参与到罢工事件中的个人、组织(如安徽同乡会、徽宁会馆、工团联合会、当地警厅),尚有一些以“评论者”身份的杂志社、个人针对这次事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其中尤其以《微音月刊》和邵力子为代表。《微音月刊》本是由徽州人士程本海、胡梦华、许士骐等发起创办,胡适与陶行知曾担任顾问,前后办四年,成为徽州同乡的喉舌,以及城乡信息交流的桥梁。[26]然而在罢工发生不久之后,《微音月刊》杂志便发表了一篇题为《社评:慰墨业工潮中的罢工同乡》[27]的文章,看似“慰问”,实则嘲讽。“徽骆驼”在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中的释义为:“徽州不产骆驼,此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28]原本对于徽州人赞誉的词汇在该文中却变成“驯骆驼”,且各种“太岁头上动土”、“自杀”、“天生贱骨”等词汇的堆积,无疑都表露了对于工人罢工行径的强烈鄙夷。而邵力子作为《民国日报》的创始人之一,[29]对于此次事件也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该报纸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于墨业工潮的两种感想》的文章,在文中我们能看到“试看墨业工人所得的工资何等微薄,此次罢工以来所受的待遇何等惨酷!”[30]这样的疾呼,可以看出邵氏对于此次罢工中的墨业工人的同情,更是对于所谓的“同乡”、“乡谊”丧失的痛惜。
就墨工这个群体而言,或许他们也明白在整个墨业并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墨店一方所陈列的理由也不无道理。可以说,墨业工人的罢工不仅仅是对于墨店的反抗,更是由于外来市场的冲击对于原本生活的震荡,他们以及墨店本身都是这场冲击的对象。进而言之,来自墨工的罢工,实则是墨业在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无论墨工还是墨店主,都在承受这一传统产业走向衰落的阵痛。徽墨的发展态势与直接从事墨业的工人息息相关,整个墨业市场的丝毫波澜都有可能对于那些墨工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墨工的罢工其原因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徽墨整体衰微的影响,但是我们实在很难将这一个当时整体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因素剔除出去。罢工表面上反映出来的是墨工为了自己的工资、工友而发动的集体性事件,但是此类集体性事件却无一不是与墨有着密切的关系。双方的关系因墨而生,此刻也因墨业市场的改变而发生了些许阻隔。也正是因为这些暴力反抗的发生,一些曾经依靠墨赖以维系生活的墨工或者被墨店开除出去,或从此南下返乡不再返回,对于两者而言这种关系的断裂是不可修复的。换言之,因为徽墨本身的衰微所带来的影响便是墨工与墨商之间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的出现。

在当前诸多的墨书当中,尤其是一些鉴赏、识别古墨的书籍当中,往往能看到大量类似经验技巧的叙述以便让读者学会识别真正的古墨而避免上当受骗。这其中所反映出的一个问题便是墨业当中存在伪墨现象。所谓的伪墨,需要进行细分,墨的伪品当中有伪造与仿造的区分。所谓的伪造指的是“为了图利伪造,墨的本身根本不是烟料,专门为骗人图利”。而所谓的仿造,“因为仍用上等颜料制成,像这样的伪品,固然不是真品,但也不能完全以伪品视之,应以仿品来看待比较公允。”[31]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曾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买伪墨的故事:“余尝买罗小华墨十六铤,漆匣黯敝。真旧物也。试之,乃抟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庭于湿地所生。”[32]其大意便是:“纪昀曾购买明朝制墨名家罗小华监制的十六铤墨,装墨的漆盒破旧,看起来是真的古物。一试,墨却是泥块,外表染了黑色,上面的白霜,也是把它盖在潮湿的地上生出来的”。从纪昀的遭遇得到的启发便是,从纠纷类型而言,上述的墨业史料缺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类型。

事实上,通过盗用、仿冒墨号等方式而从事伪墨的生产,在当时的墨业市场中非常普遍,无论是家族内部的成员还是来自其他墨店的人员都可能会因为墨号本身所蕴藏的潜在财富而卷入其中,作为消费者的纪昀也恰恰是在此经济现象中蒙受利益的损失。当然,对于墨号持有者的主人而言,同样遭受了名誉以及利益的损失,而墨店主人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是不一而足:或登报刊载声明,或注册商标,或请求官方介入进行裁决。从纠纷解决的一般程序来说,商标牌号纠纷往往是在同业内公议之后未能解决以及行规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被侵权一方才会向官府呈控,请求官方禁止假冒。[33]然而,上文关于查二妙堂墨店所遭遇的类型不一的纠纷,尤其是涉及到盗用、假冒牌号一事,即便官府多次介入也收效甚微。即便纵观今日的市场经济中,此类盗用以及仿冒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所使用的方法也不曾改变,类似“雕牌”与“周住牌”,“白猫”与“日猫”之间的文字游戏比比皆是。我们似乎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市场环境中缺少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以及与此配套的保护体系。
不过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来自外来市场的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的进入对原有市场秩序的打破与重构是徽墨衰颓的重要原因。恰如利奇所言:“社会变迁的终极‘起因’几乎总是可以归结到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但是任何变迁藉以体现的形式大部分取决于一个既定体系已有的内部结构。”[34]在整个的资本主义入侵的背景下,传统的手工作坊性质的中国墨业遭遇到了原料、机器、产品的叠加冲击[35],尽管经历了墨锭到墨汁的转变[36],仍然无法阻挡其衰败的过程。而从上文的诸多案例中可以看到,来自内部市场的诸多因素对该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困扰,其他利益群体对已成规模且声誉较好的墨号的仿制、冒用长期存在于墨业市场中。如何规范市场、保障社会秩序更好运行也成为相关群体一直所追求的目标。正如民国时期的政府、舆论界以及科学界都从不同方面积极努力试图缓解毛笔的衰颓趋势一样,当时的政府、社会、个人也都为挽救徽墨的衰微积极努力。[37]此类努力最终未能抵住其继续衰败的颓势,在各种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诸多类似查二妙堂的墨店遭遇了各种纠纷困扰却无法从根源上根除,它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甚至消失殆尽。可以说,查二妙堂墨号便是近代中国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对于查二妙堂友于氏墨业纠纷案例的关注,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出发呈现了商业过程中一种对抗性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为了打击“友干氏”的仿冒,在上文中我们看到了多种自我保护性方式的并用,毋庸置疑,这些方式对于维护友于氏墨业的顺利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 “友干氏”借用仿制墨这种方式,自然将自身与“友于氏”墨号建立起一种社会联系,原本局限于友于氏墨业的制墨此时因为其自身招牌被人仿用,导致一种人为的社会意义被赋予到墨之上。此时的墨便不再仅仅是一块供人使用的物品,而因为其制作店家的不同而被标榜上“真”、“假”的标签。就当时的社会情景来看,所有被“友干氏”生产出来的墨,都被查二妙堂友于氏墨号斥责为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谓的仿制品,或者直接称之为“假货”。墨的这种被临时建构而起的社会生命的长短取决于人们围绕着“真”与“假”的争论,以及一方的“打假”和另一方与之相抵制的程度。两者之间的争论可能会是此消彼长,也可能会是瞬间结束。就我们上述的案例而言,被赋予社会意义的墨始终伴随着这种争论而存在。
在中国墨业面临各种冲击并呈现衰颓的势态之下,那些从事徽墨生产的工人以及商家,究竟赋予了墨以何种社会意义,这是我们考察徽墨的社会生命至关重要的点。于他们而言,墨在这种状态之下,可能更多的只是与自身的生活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墨的生产、销售与否关系到的是整个墨工、墨商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本。在这个意义之上,他们表现出的一些类似于如今学界经常言及的“反抗斗争”自然值得我们的关注,借助于观察他们的反抗与否以及反抗的激烈程度,很自然地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这一时间段内徽墨发展的轨迹图。只是,无论是墨工的罢工也好,还是墨商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有这些在徽墨业整体衰颓的趋势之下都显得如此羸弱,以至于我们甚至不得哀叹,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书写工具的革新势在必行。所幸,徽墨自身的社会生命并没有因此而被中断,作为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载体,它仍旧在书写工具之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现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实行之后,此类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的徽墨制作工艺也早在2006年之时便进入保护之列,其根源就在于人们仍旧赋予墨以丰富的社会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徽墨自身的社会生命仍旧在延续着!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欢迎投稿


栏目主编的邮箱:
yunafk929@163.com
公号公共邮箱:
folklore_forum@126.com
(这个邮箱请注明新青年)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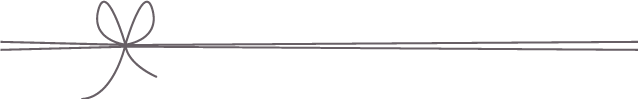
拓展阅读
65.新青年 | 谷子瑞:变与不变:技术世界中的定州秧歌 谷子瑞
64.新青年 | 中村贵:被建构的“恐惧记忆”—来自在沪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分析
63.新青年 | 姚慧:适者生存 ——京西佛事音乐中“民间音乐的佛教化”与“佛教音乐的民间化”
62.新青年 | 毛晓帅:中国民俗学转型发展与表演理论的对话关系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