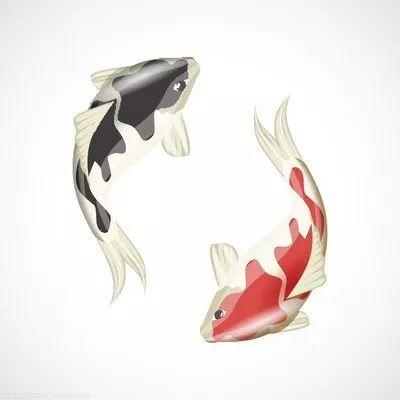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陆薇薇,女,博士,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民俗学、性别研究。本文探讨了现实及虚拟空间里“中国锦鲤”的生成过程。“中国锦鲤”是日本锦鲤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鲤鱼文化杂糅而成的“第三种文化”。

菅丰(プロファイル),男,1963 年生,1991 年毕业于日本筑波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历史人类学研究科,1998 年获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方法论的研究。
“中国锦鲤”是如何诞生的?
——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的“第三种文化”
陆薇薇 菅丰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19年02期
摘 要:现代锦鲤(Koi)的发源地为日本新泻县的二十村乡,是文化复合体的表现。随着日本全球化战略的推行,锦鲤文化从地方民俗文化被建构为日本国家传统文化,并向海外传播。当全球化的锦鲤文化流入中国时,与中国传统的鲤鱼吉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第三种文化”,即“中国锦鲤”文化。中国锦鲤文化不断发展变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出现了“中国锦鲤”“网络迷因”的衍生物。伴随着移动支付技术向全球扩展,中国锦鲤或将形成“第三种文化之第三种文化”。
关键词:锦鲤;中国锦鲤;第三种文化;祥物;网络迷因

一、引言
“中国锦鲤”是一种新兴的民俗文化,是日本“锦鲤文化”中国化的产物。它萌发于现实世界,源于两国人民对“鱼”的喜爱之情,同时又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迅速传播,成为一种聊以慰藉的网络流行文化,往往用以指代“独宠于一身的幸运儿”。
以2018年为例,“锦鲤”是人们茶余饭后趣谈的重要“梗”之一。先是在腾讯视频出品的中国首档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创造101》中一路“躺赢”取得第三名,并在之后由于孟美岐、吴宣仪的退团而成功占据 C位的“杨超越”,因为具备了锦鲤的幸运体质,被称为“人形锦鲤”,取代原本的锦鲤图案成为人们竞相转发的对象。“转发杨超越,你就能……”“今天你转发杨超越了吗?”,也成为青年人日常交际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是一位名叫“信小呆”的网友,由于参与支付宝国庆期间转发微博的幸运抽奖活动,一夜之间化身成概率仅为三百万分之一的“中国锦鲤”,幸运度超过了杨超越,成为中国锦鲤本鲤的新代言人。而这一次,信小呆不仅开启了新一轮微博、微信的转发、刷屏模式,还受到了国际瞩目,就连支付宝的全球合作伙伴都火速向这位中国锦鲤发出了跨国邀请。伴随着阿里巴巴的全球商业战略,中国锦鲤文化开始向海外渗透。
在此番锦鲤文化热潮的席卷下,人们开始梳理锦鲤的历史。他们有的把中国锦鲤史写成了一部中国鲤鱼史,重新发明出一个锦鲤文化的新传统;有的虽提及鲤变成锦鲤是在日本,却局限于科普锦鲤的生物学知识,缺乏对锦鲤文化的现代性把握。
鲤与锦鲤虽然同源,但其文化意义却大相径庭,它们在英文中的表述分别为“Carp”和“Koi”。虽然中国鲤鱼史可以追溯至八千年以前,但中国锦鲤文化的兴起不过数十载,是全球化的日本锦鲤文化与中国本土吉祥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属于“第三种文化”(third cultures)现象。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指出,在某种源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会出现这种文化不断扩张,吞噬其他文化,形成同质化的格局(第一种);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均排斥这种文化,反对其全球化,形成异质化的格局(第二种);在这样两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流动方式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文化杂糅的可能性,即这种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与地方文化相融合,跨越了民族国家间的界限,达到同质化和异质化间的一种平衡的状态。费瑟斯通所述及的“第三种文化”,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实物的交互作用为基础生成的。而今,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第三种文化”的生成不论在速度、规模还是社会影响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着重讨论“中国锦鲤”的生成问题,即现代中国锦鲤文化和作为网络迷因(Internet Memes)出现的中国锦鲤现象的生成过程及背后的原因,探究民俗文化在国际化、信息化时代所呈现出的动态性与杂糅性。
二、日本锦鲤文化的形成与国际传播
锦鲤有“水中活宝石”之称,体色大致有红、白、黄、橙、黑、蓝等几类,由于色斑艳丽、图案雅致,好似锦缎而得名。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锦鲤类属鲤科,这点经常被作为“锦鲤之中国起源说”的佐证。据有关学者研究,远在公元前12世纪的殷商时期,我国就出现了池塘养鲤,之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食用鲤逐渐遍及世界各地,也包括日本。然而,鲤鱼传到日本时,它只是鲤鱼,而非锦鲤。在日本,改良过的食用鲤呈现出了花色,此改良品种又与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其他鲤鱼品种不断杂交,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现代锦鲤。更重要的是,锦鲤不单单是生物学上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复合体的象征,围绕锦鲤形成了生产、流通、品鉴等一系列日本地方民俗文化,这种地方文化又逐渐被建构为日本国家传统文化,并向全世界扩散。
(一)锦鲤的地方史
锦鲤诞生于日本新泻县中越地区的山间。这片区域曾被称为“二十村乡”,包括现今小千谷市东部的东山地区及长冈市山古志、川口町地区。
二十村乡为大雪地带,冬季经常被冰雪覆盖,有时甚至无法与山脚下的平原地区取得联系。
当地居民为了生存,修建梯田,在水田中养殖鲤鱼。“山古志的梯田群中散落着灌溉用的池塘,人们在池塘中饲养用以食用的黑鲤。池中有‘种鲤’和‘雌鲤’之分,可见是有计划的养殖行为。插秧之后放养稚鱼,秋收之时鱼已长成,便可作为待客或过冬的食材。”养殖鲤鱼本是村落中自给自足的生计活动,未曾想却从中诞生了享誉全球的锦鲤。换言之,锦鲤文化是根植于二十村乡的地域风貌之中的。
锦鲤爱好者大多将锦鲤的起源追溯至江户时代的文化文政时期(1804—1830)。传说当时除黑鲤之外,还养殖了红鲤和白鲤,红鲤与白鲤交配产生了花纹。这一传说为曾担任新泻县水产试验所所长的越田秀包所言,他将此传说收录进其1931年编撰的《农家副业的养鱼法》中,之后被转载于各类锦鲤概说、锦鲤指南书中,然而该传说并无史料可考。据目前所能确认的一次史料记载,是在明治初期,即19世纪70年代左右,在长冈市出现了观赏用(而非食用)的彩色鲤鱼。这种鲤鱼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锦鲤,充其量只能说是锦鲤的前身,但这意味着鲤鱼不再仅仅是食物,养殖和品鉴观赏性鲤鱼的文化在该地域内开始形成。
大正三年(1914),在上野公园召开的东京大正博览会上,新泻县展出了“变种鲤鱼”(即彩色鲤鱼)。展示的初衷是扩大彩色鲤鱼的知名度,以此振兴贫困山村地区的经济,没想到不但斩获了博览会的银牌,还得到了皇太子裕仁亲王(即之后的昭和天皇)的青睐。以此为契机,新泻县的地方风物受到了日本其他地区人们的关注,拓展了在日本全国的销售渠道,为锦鲤的产业化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增强了二十村乡民众的地方认同感,为了进一步打造地方品牌,他们积极引入西方的孟德尔法则,改良繁殖技术,开始了鲤鱼的杂交培育。数年后,竹泽村的星野荣三郎成功培育出了“大正三色”品种,时任新泻县水产主任官的阿部圭将之命名为“锦鲤”。

但此后,日本社会依然存在“彩色鲤鱼”“变种鲤鱼”“花鲤鱼”等与“锦鲤”并存的说法,直至二战之后重新恢复锦鲤产业,锦鲤再次在日本全国普及以后,“锦鲤”的称谓才逐渐固定下来。1952年,新泻县开始用“新泻县锦鲤养殖渔业组合”来为鲤鱼养殖机构命名。所以,严格说来,现在人们常说的“锦鲤”一词仅有60多年的历史。
(二)锦鲤的国家化和全球化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锦鲤逐渐脱离地方语境,开始了国家化、全球化的历程。1969年,“全日本锦鲤振兴会”这一全国性机构成立,并举办了第一届全日本综合锦鲤品评会,在品评会上锦鲤被称作日本“国鱼”。这一称呼不仅与新泻县的锦鲤养殖者有关,也和出生于新泻、把新泻作为重要选区的田中角荣等政治家紧密相连,田中角荣在第一届锦鲤品评会的纪念册封面上亲笔题写了“国鱼”二字。1970年,日本举办了大阪世博会,日本政府在会场里展出了极具日本特色的庭园,由新泻、大阪、广岛的养殖者所提供的“国鱼”锦鲤也被安放其中,成为展现“和风之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作为日本文化象征的锦鲤,通过经济、文化两种途径同时向海外输出。
首先,与中国向他国赠送大熊猫一样,锦鲤作为“友好的使者”成为日本各级政府外交时的重要赠品。他们认为,锦鲤是活着的日本传统工艺品、美术品,是国家的代表。其次,日本锦鲤爱好者的组织机构不断壮大。以“全日本爱鳞会”为例,该会于1973年在美国设立了首个分会,之后在增设海外分会的同时还发行了会刊《鳞光》的英文版。再次,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日系移民积极在当地组织起锦鲤爱好者团体,例如美国锦鲤联合俱乐部(Associated Koi Clubs of America,简称AKCA )、西北太平洋锦鲤协会(Pacific Northweast Koi Clubs Association,简称PNKCA)、巴西锦鲤爱好会(Associacao Brasileira de Nishikgoi,简称ABN)等,他们举办锦鲤品评会,扩大了锦鲤在当地的影响。
在锦鲤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系移民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虽身处他乡,却心系故土,所以当作为日本“国鱼”的锦鲤文化渡来之时,他们积极接纳以慰相思。同时,象征着日本传统文化的锦鲤也成为生活在异国的这一“少数群体”确认民族身份、增强彼此间纽带的重要文化要素。另一方面,日系移民之外的当地人也给予锦鲤全球化一定的支持。例如在英国,早在1970年就以当地人为中心成立了英国锦鲤饲育者协会(British Koi Keepers Society,简称BKKS),继而于1974年又成立了中部锦鲤协会(Midland Koi Association,MKA),英国锦鲤饲育者协会规模庞大,曾拥有5000名会员。
随着锦鲤全球化的推进,目前“全日本锦鲤振兴会”的会员已遍布20多个国家,成为养殖和销售锦鲤的从业人员最主要的团体。同时,锦鲤外销至50多个国家,海外销售成为日本锦鲤的主要去向。
(三)作为文化复合体的锦鲤
如上所述,锦鲤不单单是生物学上的存在,也就是说,不是变了色的鲤鱼都是锦鲤,锦鲤身上承载着文化的要素,是一种文化复合体的表现。现代锦鲤文化是日本国家与地方协同建构而成的,它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锦鲤的象征文化。锦鲤已被建构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故而经常出现在日本庭园、大河剧、日本特产之中。本是生长在水田中的锦鲤,随着国家化、全球化的进程被重塑了历史,与传统庭园文化结合在一起。这也使得锦鲤养殖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喜爱锦鲤本身,享受锦鲤的养成过程;另一类则对培育锦鲤的池塘、庭园更加偏爱。前者会花重金购买高品质的锦鲤,热衷于参加品评会,力求取得佳绩;后者则将锦鲤视为庭园的一部分,属于欣赏庭园之美的余兴,对锦鲤品评会的成绩不太在意。除庭园外,锦鲤之所以在大河剧及面向外国人销售的日本文化特产中频频现身,也是出于不断建构其悠久历史并巩固其“国鱼”的合法性身份的需要。
二是锦鲤的生产文化。养殖锦鲤起初是新泻县的地方行为,之后先是引起了日本其他地区一些富裕人士的关注,继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日本民间爱好者的增多而逐渐趋向产业化。锦鲤养殖技术主要依靠不完全的系统交配和个人的筛选经验,娴熟的技术是日本锦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锦鲤的筛选技术是生产优质锦鲤的关键所在,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地的生产者依然络绎不绝地赴日拜师学艺。
三是锦鲤的品鉴文化。锦鲤虽是由食用鲤演化而来,却不再被食用。作为一种高档观赏鱼,锦鲤的品鉴文化在文化复合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锦鲤的欣赏、品鉴和评价体系均参照日本的标准。具体来说,有100种以上的锦鲤品种名称是用日语表述的,评判的基准也由日方决定,分为体型、色彩、图案、质素等。由于评判的标准极为抽象,主要依赖于评委个人的审美情趣,而日本的规则又是世界标准,所以世界各地的锦鲤品评会上,日本评委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可以说,象征、养殖、鉴赏的文化复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日本锦鲤文化。在锦鲤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它是以这样一种复合体的形态向外扩散的。2000年以后,随着日本“Cool Japan”计划的推行,日本推广文化软实力的势头加剧,锦鲤文化也变得更加国际化。

三、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
继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之后,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Watson)在《东方金拱门》一书中结合麦当劳的个案对“第三种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当全球化的麦当劳遇见东亚的地方文化时,它发生了地方转型。这种地方转型与地方主体的能动性密不可分,他们有意无意地重构了麦当劳文化,打破了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这一全球统一标准。同时,当地的文化也因为麦当劳的存在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跨越两者间的边界、在两者间动态互动着的“第三种文化”。与此类似,中国锦鲤文化是对全球化的日本锦鲤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再建构。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有意无意地重构了日本锦鲤文化,赋予了其中国传统鲤鱼文化的新内涵,这打破了日本锦鲤文化复合体的固有形态,同时也对中国鲤鱼文化带来了一定冲击,形成了“中国锦鲤”这种跨越中日两国之间的界限而不断互动、杂糅的“第三种文化”。
(一)中国鲤鱼与吉祥文化
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文化的形成,是与中国鱼文化悠久的历史积淀密不可分的。陶思炎还对中国鱼文化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中国鱼文化作为我国民间最见习的行为模式和象征符号,体现在物质成果、仪礼制度和精神活动的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所有领域。”陶思炎对鱼文化的功能类型作了归纳,即包括图腾崇拜、生殖信仰、丰稔物阜的始生导向,辟邪消灾、星精兽体、世界载体、沟通天地与生死、阴阳两仪、通灵善化的外衍导向,以及巫药占验、祭祀祝贺、游乐赏玩的内化导向。
在众多的鱼类当中,作为祥瑞动物的鲤鱼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地位,是鱼文化的重要代表。它曾与道教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琴高乘鲤涉水,子英乘鲤升天”之说;亦曾被奉为唐朝“国鱼”,受到统治阶级的尊捧。正如金泽所言:“在传统社会,民众普遍参与的某些民间信仰形态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并不完全是民众自发的行为产物,这与社会上层,特别是统治集团的有意推助密切相关。”可见,鲤鱼之所以能成为民间普遍性的吉祥物、受到民众的崇拜,是与其在宗教、国家等权威话语体系中被赋予的“神圣性”紧密相连的。唐朝之后,鱼文化加速走向大众化、日常化、民间化,赏鲤馈鲤、以鲤为符等达官贵人、文人骚客的雅趣逐渐在百姓中传播开来。以鱼龙图为例,该图案本是用来表达鱼与龙具备相似的特性和神能、可以相互转换的含义,但随着鱼文化的脱“圣”入“俗”以及“‘鲤鱼跳龙门’的图样在民间大量出现,成为年画、挂笺、刺绣、木雕、印染、剪纸等民俗艺术品中常见的传统题材,反映了时人偏好祥瑞图与吉祥物的民俗心理,以及逐步凸显的追求腾达的市民情趣”。


鲤鱼成为祥物之后,更加贴近于百姓的日常,成为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寄托。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除了“鲤鱼跳龙门”的成名之愿以外,还有“年年有余(鱼)”年画中男孩怀抱的象征着丰稔、富庶的大红鲤鱼,表达对爱情的美好祝愿的“喜结连理(莲鲤)”中的鲤鱼图案,祭祀财神以求通达的鲤鱼供品,以及池塘中供人观赏的红鲤,日常馈赠亲友的鲤品等等,鲤鱼文化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吸纳和重构日本锦鲤文化的基础。
(二)中国锦鲤文化的生成及特征
鲤鱼的民俗文化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日本锦鲤文化流入中国之时,人们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将锦鲤作为“他者”的异文化加以对待,而是在与日本锦鲤的异文化的碰触中呈现出“自我”的表征,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锦鲤文化。
如上所述,日本锦鲤文化主要包含了象征、生产、品鉴的三重维度,是三位一体的综合体现,在中国语境中这三重维度的文化内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杂糅。
首先,从象征文化的维度来看,被建构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与日本庭园合为一体展现和风之美的锦鲤,被直接置于江南园林里,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之中。例如在上海豫园中的庭园、玉佛禅寺觉群楼前的池塘里,都游动着色彩斑斓的锦鲤。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游乐赏玩的花鸟鱼虫文化,池塘中原本也有红鲤鱼、金鲤鱼的存在,所以观赏者对日本锦鲤的到来丝毫没有违和感,或者说感觉它们的存在仿佛是理所应当的,是自古就有的。不仅如此,在玉佛禅寺净意谭边有关锦鲤的介绍中,人们寄托于鲤鱼身上的对日常生活的美好愿望被顺理成章地依附到锦鲤身上。例如,头顶红斑的红白丹顶锦鲤被喻为“鸿运当头”,由红、白、黑三色组成的大正三色锦鲤被称作“三慧合集”,成为求财求缘的象征等等。
除中国的传统园林之外,在人群聚集的公园、博物馆、风景名胜之地,宾馆、餐厅的水池中,车站、机场的宣传画上,甚至在工艺、美术创作的世界里都不乏锦鲤的身影。例如,原本在寓意吉祥的中国国画中,常常出现的是黑鲤鱼和红鲤鱼的组合构图,现在却不乏锦鲤的身影。在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中融入锦鲤这一形象的“创新”,恰恰反映出日本锦鲤文化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人们对鲤鱼与锦鲤的等同、混杂使用。更重要的是,这种鲤鱼与锦鲤的杂糅,不仅意味着对锦鲤的无意识本土化建构,同时也赋予了锦鲤新的吉祥文化内涵,这是作为日本文化复合体的锦鲤不曾具有的象征意义,是其在中国语境中与中国鲤鱼所代表的吉祥文化融合的结果。
其次是锦鲤生产文化维度的交融。在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有众多锦鲤爱好者。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为了振兴经济,也积极推进锦鲤产业的发展。例如广州市周围的顺德、中山、江门等地区建有大型的锦鲤池,江门市还在2009年被中国渔业协会指定为“中国锦鲤之乡”。由于锦鲤生产的特殊性,锦鲤养殖指南类的书籍多是日文的译著,但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中国锦鲤爱好者自主编写的锦鲤养殖实用技法类的书籍。在这些书籍中,会有一些对锦鲤文化的概述,然而在肯定锦鲤的发源地为日本的同时,都会千篇一律地强调锦鲤的祖先是鲤鱼,而鲤鱼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这实则是在强调锦鲤的“根”在中国,锦鲤文化根源于中国文化。这种对锦鲤历史有意识地再建构与扩大中国锦鲤产业的经济战略密切相关,是激发锦鲤爱好者、养殖者的民族自豪感的有效途径。
再者,从锦鲤的品鉴文化来看,中国的锦鲤爱好者以企业家、投资家等富裕人士居多,他们对锦鲤本身的价值极为重视,往往耗费巨额的资金,与其他观赏类的动植物、古董、美术品等投资有类似之处,这也决定了他们会基本依据日本所制定的世界标准来进行品鉴。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的锦鲤品评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例如将黑白花纹品种的锦鲤大奖命名为“水墨国画奖”,显然是将锦鲤身上的图案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意境有机结合在一起。
综上所述,当作为日本文化复合体的锦鲤“游”来中国后,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建构。颇有意思的是,以锦鲤爱好者为主,对锦鲤生产文化与品鉴文化的“有意识”的调试,并未给标准化、全球化的日本锦鲤文化带来多少冲击,反倒是普通民众在象征层面对锦鲤文化的“无意识”的重构,打破了锦鲤文化的全球化标准,使得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文化形塑而出。而这种中国锦鲤文化能够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锦鲤”和“中国鲤鱼”的相似性、亲缘性,这种相似性、亲缘性使得国人对于外来的锦鲤文化没有过多的抵制,较为自然地将其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中,并赋予它与鲤鱼同样的吉祥文化的内涵。同时,我国的鲤鱼文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鲤鱼与锦鲤的混同。“第三种文化”是“超越国界的”,它不再一味地追问文化的起源,而是将目光转向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关注文化杂糅的动态过程,这种杂糅性、互动性正是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文化的特征所在。
四、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锦鲤
中国的鲤鱼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民间基础,这使得由日本锦鲤文化本土化建构而成的中国锦鲤文化在民间迅速蔓延开来。并且,伴随着移动媒体在中国爆发式的增长,虚拟空间中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文化进一步演变,不论在速度、规模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都远超其在现实空间中的体量,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出现了锦鲤迷因(Koimemes)的衍生物。
(一)中国锦鲤的符号化与神格化
中国锦鲤文化的核心在于“吉祥”,与鲤鱼的民俗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虽然在文化杂糅的过程中人们延续了日本锦鲤生产文化、品鉴文化维度的大部分内容,形成了中日锦鲤爱好者间的良性互动,但最为中国普通民众所广泛接受的却是日本锦鲤文化中未曾包含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幸运”的象征内涵。
在此背景下,近几年来转发锦鲤祈求好运的网络民俗成为热潮,形成了中国锦鲤文化的衍生物——中国锦鲤迷因。根据笔者从微博上收集的资料显示,转发锦鲤最早出现于2013年5月,而一个名叫“锦鲤大王”的大V账号对转发锦鲤热的形成有重要推动作用。2013年7月19日,该账号发出了第一条微博,称“关注并转锦鲤图者一个月内必有好事发生”,截止至2018年11月,该条微博已被转载93万余次。

2013年至今的锦鲤图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日本锦鲤图,第二类是中国鲤鱼图,第三类是人形锦鲤图。第一类和第二类分别是对日本锦鲤之吉祥象征意义的重构以及日本锦鲤文化冲击下出现的鲤鱼和锦鲤的混同,这与上文所述的现实生活中生成的“第三种文化”无异,是中国锦鲤文化在虚拟空间的延伸。然而第三类的人形锦鲤图(一些综艺明星、话题人物与锦鲤、鲤鱼的结合图)中包含了很多流行文化的“梗”,是中国锦鲤文化的新的演变,成为2018年最受欢迎的转发对象。
锦鲤图
戴望云指出:“当传统文化和互联网发生冲突时,变革不可避免。尽管名叫锦鲤,但是许多现代锦鲤迷因根本没有鱼的特征。相反,它们经常围绕一个成功人物,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获得期待已久的奥斯卡奖之后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或者是一个被认为特别幸运的人,比如2018年一部人气电视剧中无情的玛丽苏式女主角魏璎珞。偶尔这些人物的形象也会被编辑得像鱼,但通常它们与实际的锦鲤只有微弱的联系。”可见,在网络世界里,锦鲤已逐渐演化成了一种“幸运符号”,其形象是日本锦鲤还是中国鲤鱼变得不太重要,它甚至已经不再出现于锦鲤图之中。然而当锦鲤只剩下“锦鲤”二字之时,我们或许也会逐渐遗忘中国锦鲤文化的生成过程,跳过中国传统鲤鱼文化与日本锦鲤文化的杂糅阶段,直接将中国锦鲤迷因作为传统鲤鱼吉祥文化与互联网技术碰撞而生成的产物。
同时,随着人形锦鲤图的蔓延,“拜锦鲤教”也开始出现。虽然自2013年起就有人形锦鲤图,但说到锦鲤本鲤崇拜,不能不提2018年的话题人物“杨超越”。董牧孜分析了年轻人拜杨超越的情感结构和心理特征,认为杨超越的走运是与她同样焦虑的群体的“精神安慰剂”,而拜人形锦鲤现象的本质是后现代式的戏谑,是明知其荒诞而为之。其实,这种现象也不是当下才有,早在转发锦鲤之前,年轻人就曾将李宇春等“幸运”的选秀明星捧上神坛,“2008年‘信春哥、不挂科’的顺口溜流行于网络,2009年对‘考神’李宇春祈愿开始成为热潮”。民俗具有心理调适的功能,网络民俗更是如此,至于灵验与否祈愿者倒不是十分在意,只是寻求心理安慰罢了。如今,融入锦鲤这一元素之后,祈愿的内容更显多样化,比如“考试前夜拜杨超越,想要打败情敌则拜魏璎珞”。然而,不论是学业有成、事业进步,还是财运亨通、爱情美满的祈求,都可以从上文所述的中国锦鲤(鲤鱼)的传统寓意中找到印证,就连人形锦鲤的神格化也可以从鲤鱼曾经拥有的神圣性中寻得关联,这种中国锦鲤文化的新的演变实质上并没有跳脱传统文化的语境。
可以说,人形锦鲤是中国锦鲤网络迷因的一种,也是目前最受关注的文化潮流,这种文化的承载者主要是年轻人,它的变异性较强,愈发脱离了实物的鱼,愈发褪去了锦鲤的日本语境,将其变为符号化、神格化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它还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锦鲤迷因相较一般的网络迷因而言,蕴含了更多的传统性,这也使得它比稍纵即逝的其他网络迷因存续的时间更长,影响的范围更广。
(二)中国锦鲤的商业化与国际化
2018年的四大人形锦鲤分别是杨超越、魏璎珞、信小呆和棠福蘆。依笔者所见,前两者和后两者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特征区分,即从信小呆开始,中国锦鲤迷因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信小呆是支付宝国庆期间选出的“中国锦鲤”,棠福蘆则为天猫“双十一”10周年晚会抽中的“欧气锦鲤”,两者都与阿里巴巴的商业战略捆绑在一起,可谓民俗经济的产物。吴玉萍认为:“企业节日必须有民俗行为的支撑,这种行为体现在节日符号的设计、带有民俗元素产品的开发以及民俗平台的打造等。只有通过这样的民俗实践,企业节日才能有效形成。”趁着网络上转发锦鲤的热潮,将锦鲤元素融入蜂鸣营销(Buzz Marketing)中,无疑是阿里巴巴2018年极为有效的民俗实践,它增加了民众的认同感,在国庆期间创造了企业传播案例中迄今为止总转发量最高、企业营销话题占据微博热搜榜单最多的纪录,并在双十一当天刷新了之前的销售额,2018年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全天成交额最终突破2000亿元。同时,阿里巴巴的民俗实践也给中国锦鲤文化带来影响,信小呆的热度迅速超过杨超越、魏璎珞,成为新一轮锦鲤代言人。不仅如此,在商业化的影响下,中国锦鲤的概念及意象被进一步确立,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文化开始走向世界。
虽然笔者在本文中为了区分中国锦鲤文化和日本锦鲤文化,始终在锦鲤之前冠以“中国”两字,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对锦鲤与鲤鱼的混同,或者说认为锦鲤就是传统鲤鱼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文化的特征),所以信小呆出现以前,网络上流传的都是“锦鲤”一词,没有“中国锦鲤”一说,是支付宝的“中国锦鲤”活动使这种说法普及开来的。活动之后,网络上出现了“转发……,下一个‘中国锦鲤’就是你”之类的信息,商家们开始争相效仿支付宝的活动,打造出“成都锦鲤”“杭州锦鲤”等中国地方锦鲤。从意象上来看,支付宝“中国锦鲤”的图标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火红的背景上跳跃着一条金鳞红鲤。虽然上文中反复述及中国锦鲤文化中锦鲤与鲤鱼的混杂、混同现象,如池塘中并存的锦鲤和鲤鱼,网络上同在的锦鲤图、鲤鱼图等,然而支付宝的图标设计极富冲击力,似乎在昭告天下这才是中国锦鲤应有的姿态。加之其巨大的影响力,于是,杨超越的表情包里偶尔闪现的色彩斑斓的锦鲤到了信小呆的表情包里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中国鲤鱼,而其他商家的“双十一”宣传画也大多模仿了支付宝中国锦鲤图标中的中国意象。
同时,伴随着阿里巴巴的全球战略,被其建构的愈发中国化的中国锦鲤文化开始向境外、海外传播。中国锦鲤文化是日本锦鲤文化向全球扩散时与中国传统鲤鱼文化相融合的结果,虽然在互联网空间中形成了转发锦鲤祈求好运的中国锦鲤迷因,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但基本是国人自娱自乐的一种地方性文化。然而由于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移动支付技术在全球的推广,包含于其中的民俗文化要素也开始“渗透式”地对外输出,中国锦鲤文化的商业化和全球化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在信小呆当选“中国锦鲤”之后,支付宝的全球合作伙伴纷纷向其发出邀请。2018年10月10日,搜狐网刊登了《一条“中国锦鲤”的英文,竟然难坏了这么多国家的人》的趣文,对世界各地的一些机场及购物场所中“中国锦鲤”的相关描述做了调查,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譬如,香港国际机场用了一红一黑两条鲤鱼的传统吉祥图像及“luckfish”这样一个体现中国锦鲤文化“幸运”的核心内涵的词汇加以描述。迪拜机场和欧洲的比斯特购物村则直接选用支付宝的中国锦鲤图,在文字表述上,迪拜直接使用了“中国锦鲤”的中文字样,比斯特购物村除了“中国锦鲤”外,还加上了“Chinese Jinli”的英文表达。公共空间中的这些展示,潜移默化地宣传着由支付宝建构的愈发中国化的锦鲤文化,将锦鲤的英文表述为汉语发音的“Jinli”而非日语发音的“Koi”是其最为突出的表现,也是支付宝国际影响力的一种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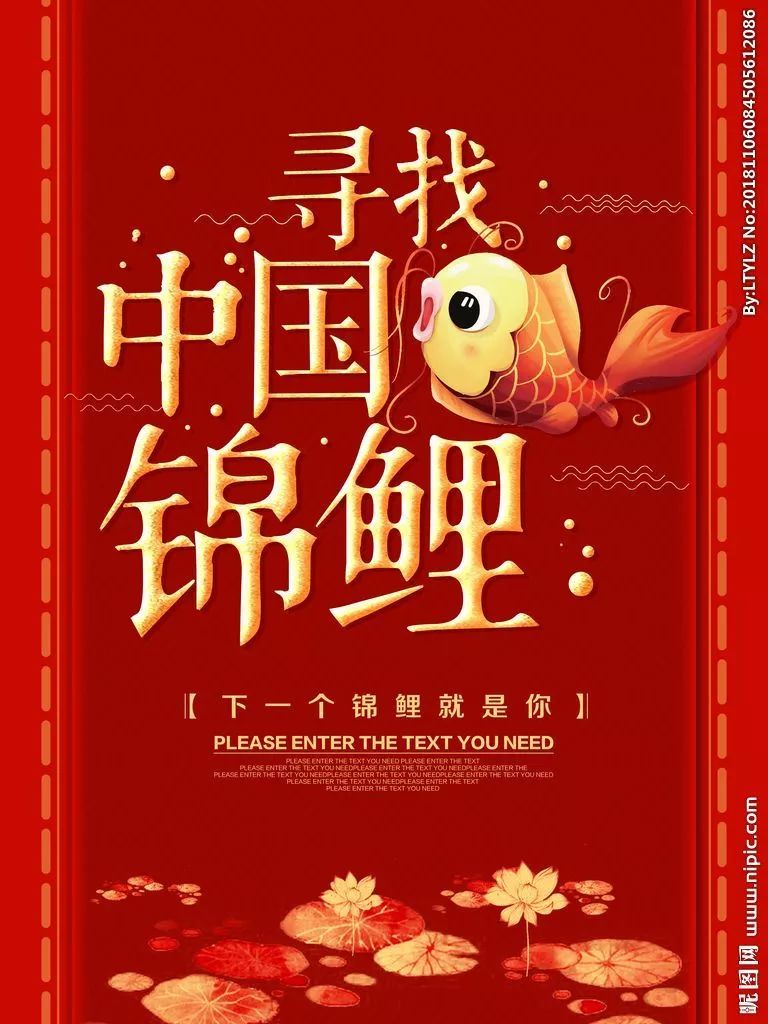
另一方面,该文提及的日本药妆店和法国巴黎春天商场门前的图片中,出现的依旧是色彩斑斓的锦鲤的身影。在锦鲤原产国的日本,若将其表现为红色鲤鱼或许会有指鹿为马的感觉,而法国保安手中的锦鲤则暗示着日本锦鲤文化已在法国有了一定的影响。显然,当“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文化向全球扩散时,我们不仅将面对与当地(尤其是锦鲤原产国日本)本土文化的碰撞,在那些已经受到日本锦鲤文化影响的国度,中日锦鲤文化也将发生冲突,文化的杂糅会进一步加剧,中国锦鲤文化可能被重构,或将形成“第三种文化之第三种文化”。
五、结 语
本文探讨了现实及虚拟空间里“中国锦鲤”的生成过程。“中国锦鲤”并非中国的固有文化,它是日本锦鲤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鲤鱼文化杂糅而成的,是一种“第三种文化”。
“锦鲤”一词出现于大正时期的日本,但锦鲤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大约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从一种地方风物被建构为日本“国鱼”,作为文化复合体包含了象征、生产、品鉴三重维度。
中国有着悠久的鱼文化历史,鲤鱼作为其重要的代表,历经了由圣入俗的过程,成为民间普遍性的吉祥物,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为“中国锦鲤”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由于鲤鱼与锦鲤的相似性、亲缘性,日本锦鲤文化袭来之时,除了中国的锦鲤爱好者在生产和品鉴维度对其进行有意识的重构以外,民间还无意识地赋予它与鲤鱼同样的吉祥文化的含义,并为传统的鲤鱼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出现了鲤鱼与锦鲤的混同,形成了不断互动、杂糅的中国锦鲤文化。

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新的演变,形成了转发锦鲤祈求好运的网络迷因。当下,“人形锦鲤”迷因最受关注,它既是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将锦鲤“符号化”“神格化”的产物,也是资本刻意经营的结果,由于腾讯网和支付宝等商业因素的介入,因而呈现出典型的商业文化民俗化的特征。这些演变的共通之处,在于让中国锦鲤变得越发贴合中国传统、脱离日本语境,而锦鲤迷因蕴含的传统性也使得它日益拥有更加广大的受众面。
同时,越来越富含中国元素的锦鲤文化,伴随着支付宝的全球战略而开始趋向“国际化”。迈克·费瑟斯通和华琛虽然在研究中注意到某种源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与地方文化互动、杂糅而形成“第三种文化”的现象,但他们却忽略了“第三种文化”持续发展,进而演变成为源文化,与原有的源文化并存或将其颠覆的可能性。中国锦鲤文化的演变便是这种可能性的一个有力例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文化的生产与接受的主客二元对立被打破,两者会不时地交换位置,这种流动性需要今后的民俗文化研究更为关注。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9年02期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拓展阅读
101.新青年 | 郭周卿: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研究 (1904~2018)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