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于洋,男,辽宁辽阳人,人类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专业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宗教民俗学,历史民俗学。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的《通古斯人心智丛》(psychp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为萨满教研究史上的经典著作,是史氏在其“心智丛”理论框架下对通古斯人萨满教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成果,开创了在“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的整体视野中对萨满教进行理解和说明的范例。本文对史氏萨满教研究的学术遗产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以期对反思、推进我国的萨满教研究有所助益。
史禄国和他的通古斯萨满教研究
于洋
原文发表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02期

史禄国(S.M.Shirokogoroff)的通古斯萨满教研究有其自身的前提、起点,以及由这两者构成的与同时代和前辈学人之间的对话。粗略而言,我们可以将其萨满教研究的主要贡献理解为对“萨满教病态心理学派”提出挑战,强调萨满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是健康的人。但在方法论方面,史氏萨满教研究的几个鲜明特点是以往同类萨满教研究著作所没有的。
首先,在关于理论传统的承继和对话上,史禄国的视野没有局限在萨满教自身的研究传统,而是在其民族学的ethnos理论、“心智丛”(psycho-mental complex)概念的框架下展开的;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史禄国给予文化持有者观点以极大的尊重,他自觉采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和访谈法,与调查对象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族群主位观的基础上理解通古斯人的萨满教文化丛,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对萨满教的理论阐释;最后,在研究旨趣上,史禄国从文化整体观的立场,系统说明萨满活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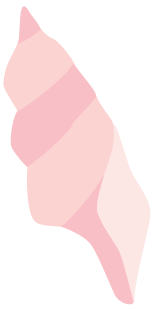
一
史禄国的民族志作品是自成系统的,这些作品的写就是基于他在通古斯人中长达6年之久 (1912年至1918年)的田野考察,不同时期的文本处理了语言、社会组织、宗教等不同方面的主题, 并且彼此之间构成“互文性”关系。其萨满教研究主要体现在《通古斯人的心智丛》(1935)中,本研究以该著作为对象,试图对史禄国萨满教研究的基本思路进行梳理和评价。

史禄国
“心智丛”概念贯穿了史禄国萨满教研究的整个研究过程,它是史氏萨满教学说的基础。在史禄国的文本中,他对这一概念的建构动机进行说明。史禄国的问题意识源自当时英国进化论学派和法国社会学派的“民俗”、“宗教”研究。他认为, “进化论学派中存在一种“与‘文明人’相对应的 ‘原始’、‘未开化’、‘野蛮’的假设”[1],这个假设实际为调查者自身族群的文化观念,在研究过程中, 他们会对观察到的材料进行有意或无意筛选。另一方面,史禄国也注意到,像“民俗”、“宗教”之类的民族学研究主题过于单一,它们是族群单位整体文化丛中一个构成部分,应还原到完整的族群心智现象层面进行理解。在这一研究思路上,他提到了列维·布留尔(Lvy-Bruhl)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相关研究。在史禄国看来,列维·布留尔虽然在族群整体心智层面进行研究,但是“他的理论是欧洲文化自身的一个理论,与进化论的假设相一致,认为人类经历了‘前逻辑’阶段,并通过马赛克似的工作筛选事实对理论进行构建”[1]9。 相比之下,他对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概念表示出更多的赞同,并且同意涂尔干将这一概念视为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但史禄国不同意涂尔干将“集体意识”视为有自身机制和生命的超有机体现象, 而是认为这一事实与物质环境、社会组织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沿着这一思路,史禄国提出了“心智丛”概念:
它是指一些文化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在对特定环境适应过程中在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反映,其中特定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我将这些文化要素分为两组,即是 (1)一组反映态度,这些态度是持久的、明确的,虽然在特定的范围内会发生一些变动;(2)一组观念,这组观念表明了特定的精神态度,同时它们也是特定族群单位或个人的理论体系。[1]1

由于“心智丛”是特定族群在对环境适应的过程中的反映,所以史禄国对“心智丛”在特定族群单位的文化丛的位置、变化规律以及功能分别进行说明,这关联到他所提出的民族学ethnos理论。
作为现代民族学的奠基人,他对民族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为了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政治色彩,他借用源自希腊语的ethnos一词来表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相信自身有着共同的来源,共享一套习俗与社会系统,并有意识地维系着习俗与社会系统,将其解释为传统,这个单位的文化的和体质特征的变化都在其中发生。”[2]在史禄国那里,每一个etnnos在对基础环境(气候、地貌、植物群、动物群)适应的过程中会形成特定的技术文化知识;随着与基础环境间关系的复杂化,ethnos会进而创造了“派生环境”, 这个环境在本质上是文化产物,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方面的知识;ethnos还有第三类环境,是指它在与其它族群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族际环境”。 因此,民族学研究单位ethnos的形成,取决基础环境、派生环境以及族际环境。
由于上述三种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所以ethnos不是一个静态的单位,而是始终处于变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ethnos文化的、(身体)形态学的、“心智丛”的变化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史禄国认为,ethnos的文化创造和延续主要体现在心智层面的活动上,表现为具体的态度和观念。 每一个ethnos都有独特的“心智丛”,是ethnos整体的一个功能部分。“心智丛”保证了或者说更好地说明了ethnos的存在,发挥了适应变动环境的功能,使ethnos足够敏感,通过对环境的适应、抵抗或者变通,实现自身的再生产。
二

根据ethnos理论的基本框架,史禄国考察了通古斯人的“心智丛”。他发现,“通古斯人是很好的观察者,与欧洲人相比,他们得出结论的方法并不缺乏任何逻辑要素”[1]403,通古斯人对周围环境的态度和观念遵循“观察—假设—试验—结论”的逻辑,对于比较重要的结论,他们会不断地进行检验和修正。
史禄国发现,通古斯人对基本环境的认知抱持实证主义的态度。他调查了通古斯人对于地球天体、季节、时空观念、距离观念、植物群、动物群的认知,并证明了通古斯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是实证性的,是与通古斯人的狩猎生计方式相适应的。
在对派生环境的适应上,史禄国发现,“社会组织这一事实并没有进入到通古斯人的意识之中,只要社会组织作为整体而存在,就不会被触及和改变”[1]216。史禄国认为,只有社会组织以十分显著地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才会引起通古斯人心智层面的注意。因此,他认为通古斯人在对“派生环境”的心智表现主要包括对亲属称谓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权力、义务方面的认识。
通古斯人对“族际环境”的“心智丛”方面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对与其相毗邻的族群单位的认知上。其它族群单位成员的体质特征、语言、服饰等方面都会进入到通古斯人的视野之内。跟据史禄国的调查,在这一方面,通古斯人一方面承认自身的优越性(如狩猎、驯鹿和审美等),另一方面也承认其它群体具有优势的方面。因此,他们“不会受到族群中心主义的影响,他们对族际环境之间的分析很复杂,尤其是历史方面、语言方面已接近客观”[1]167。

根据史禄国的观点,通古斯人“心智丛”方面的态度和观念形塑是基于实证的原则,上述三方面知识是客观的,具有实证的性质。但是,就像在其它族群中所遇到的情况那样,通古斯人也会遇到一些事实,他们不能将这些事实的解释整合到一个整体的实证系统之中,出于心理认知需要,通古斯人会将这些解释建立在一些假设上。这一建构逻辑与已有的实证知识间并不矛盾,它们遵循着同一个更基本的原则,如果这些假设能证明与实证知识相适应,就会逐渐为族群成员所接受。
在通古斯人的假设知识中,关于灵魂和神灵的假设是其中之一。史禄国认为,通古斯人萨满教文化丛是由这一假设衍生而来。史禄国首先考察了通古斯人中围绕着神灵和灵魂这一假设所衍生出来的整体文化丛,它包括了不同层次的文化表现。在观念层面,这一文化丛包括了在三界宇宙观基础上形成的神灵观念,史禄国尤其提到了通古斯人关于神灵“路”的观念,这些神灵具有不同的时间、方位,有的源自通古斯人之中,有的则借自其它的族群单位(包括汉人、蒙古、俄国人)。 在行为实践层面,通古斯人与神灵的“沟通”主要是令神灵凭依神位,然后献祭。其中献祭手段主要包括祭品(杀死的动物、水果、酒等)和祭词。在实践主体层面,史禄国区分出三种情况,就与神灵 “沟通”而言,有些神灵是所有人都可祭祀的,有些神灵则需要特定的献祭人员,有一类与神灵的“交往”活动,只能由通古斯人中的萨满来完成。他将围绕着萨满所形成的文化现象群归为“萨满教”, 因此“萨满教”是嵌入在通古斯人围绕神灵和灵魂观形成的信仰生活的一个构成部分,这构成了史禄国萨满教研究的背景和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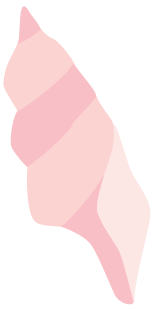
三
史禄国眼中的萨满教是通古斯人在自身“万物有灵”的环境中孕育出的一组特殊的文化丛,这组文化丛是围绕着萨满所建构起来的,它包括如下的要素:(1)萨满是神灵的主人;(2)萨满控制一定数量的神灵;(3)萨满知晓与神灵交往的手段; (4)萨满拥有被认可的神器;(5)萨满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6)萨满具有特殊的社会位置;(7)萨满具备进入迷幻状态(extasy)的能力,这些社会文化方面和生理—心理方面的特征共同构成了史禄国对萨满教的定义[1]271-274。
正如史禄国对民族志研究所设立的期待那样,这门学科“既包含功能又不抛弃历史,既关注族群单位内部又关注族际关系”[3]。对于“萨满教” 这一文化丛,史禄国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和说明。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将萨满教定义为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相对应的宗教形态的泛化表述,进而在进化论的框架下将萨满教定义为“原始”宗教的做法。他更倾向于将萨满教的定义建立在具体族群单位材料基础上所提炼出来的典型文化要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文化丛的产生、 变迁以及功能进行分析。
首先,史禄国对通古斯人萨满教文化丛的“起源”问题进行考察分析。在这方面,他主要从萨满教文化丛中的神灵观念、萨满器物两个方面来说明通古斯人萨满教的起源问题。神灵假设是通古斯人萨满教的基础,史禄国试图通过通古斯人的口碑传说发现萨满教起源的线索。他认为,虽然不能将通古斯人萨满教的解释视为历史事实,但是这些讲述提供了一些稳定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萨满教的神灵往往来自于其他族群,有些神灵还保持着它们在其他族群单位中的名称,它们大多是佛教的神灵。在萨满器物方面,史禄国主要考察了通古斯萨满实践中必不可少的萨满器具铜镜,铜镜主要从蒙古人、汉人和西藏人中购置,而铜镜是佛教中的主要器物。接着,史禄国转向历史文献,他发现佛教在通古斯人中的影响主要发生在辽金时期,主要的中介为达斡尔人的祖先契丹人,然后传播到通古斯人中。据此,他对通古斯人萨满教的“历史起源”进行了如下推测: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佛教开始渗透到通古斯人中,由于政治上对佛教的排斥,所以一般的通古斯人群中开始出现“模仿”僧侣支配神灵的人物,因此,通古斯人的萨满教文化丛是在佛教刺激下产生的,是通古斯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发明”。不过他也承认,“通过佛教刺激的萨满教起源可能永远都是假设,随着这方面分析的增多,假设的正确性会逐渐增加;但是它的假设性质可能不会发生改变”[1]285。

其次,在史禄国那里,他区分通古斯人萨满教文化丛的两类问题,“一类涉及的是有萨满社会里 ‘精神错乱’的形式和性质,另一类涉及的是萨满的职能与个人人格之间的关系”[4]。他考察了通古斯人群中的一般心智状况。史禄国反对博格拉兹 (V.G..Bogoraz)、查普利卡(Czaplicka)等人过于概括性地将包括通古斯人在内的西伯利亚地区各族群中所见到的各种“异常”的精神行为现象称为 “北极歇斯底里”,史禄国发现,通古斯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异常心智行为表现可以被归入到病理学的范畴之内,而很大一部分“异常”的心智现象在史禄国看来都是社会文化现象,他特别提到了通古斯人中有一类被称为“沃伦”(模仿性的疯癫) 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模仿说一些社群所禁忌的语言、行为,例如模仿别人的动作、模仿一个人的淫秽语言、公开场合模仿别人的性行为,民族志研究者一般将这些现象视为病理学现象。史禄国则认为,“沃伦”现象从病理角度解释是不会成功的, 虽然他们解释了病人的心理机制,“但是对隐藏在 “病理学”背后的原因还是隐藏不见的”[1]31。他发现,这些“沃伦”现象背后包括了社会认同或者不认同的现象,后者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社会可以停止或者发展“沃伦”现象。因此在史禄国看来, “沃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社会环境刺激下主体将自身认同为“表演者”的现象。
在类似的现象中,通古斯人将一类现象看作 “神灵附体”。他观察到,受到神灵影响的人往往会表现出“(1)躲避阳光;(2)坐在地上或者炕上; (3)哭泣或者歌唱;(4)逃离与返家;(5)藏在石头中;(6)爬树并且在树干上跳跃”[1]251等。这些标志性的现象是通古斯人所厘定的神灵“选择”萨满的传统习惯模式,候选者往往借助暗示等手段表现出上述特征,如果他们能够“掌控”神灵的话,就会被选择为萨满。史禄国的调查结果告诉我们,病理学意义上的通古斯人的精神错乱行为是很少见的,在一般民族志者定义的“精神错乱”现象在通古斯人那里往往是“正常”的,是他们社会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因此这些现象背后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原因。产生上述行为的人是有意识的,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个体可能发生了严重的疾病、早孕、 各种各样焦虑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在社会集聚的场合发生了此类行为。根据史禄国的观察,往往在这样的一个放松过程之后,个体的平静和满足感就会恢复。社会不会敌视这些“神灵附体”的人,并且给予这些人以关注,社群的成员都会对这个人感兴趣、谈论此人并且询问关于这个人的一些信息。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可能逐渐地成为社群中的重要成员,因为这些人是与神灵联系在一起的,神灵可以通过这些人进行言说,萨满通常从这些人里产生。
在通古斯人中,萨满的产生要具备进入迷幻能力的前提。史禄国介绍到,通古斯人中萨满的产生主要存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主要见于后贝加尔地区,氏族成员会在处于青春期阶段、具备进入迷幻能力的青年中选择一个人作为萨满候选人,由氏族的老萨满用数年时间培养,最后氏族要为新萨满举行承认仪式;另一种情况被称为“神选”,主要见于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和满族人中, 这类人由于神灵附体而受到困扰,表现出被神灵附体的一系列固定特征,经过有经验萨满的“治疗”和教导,在氏族成员认可的情况下,这些人最后成为萨满,并举行承认仪式。通古斯的萨满往往能掌控一定数量的神灵,对于氏族萨满来说,他们要掌控氏族神灵以及各种各样的外来神灵,萨满要借助自己掌控的神灵来抵御威胁氏族成员的神灵。通古斯萨满的服饰和法器是萨满对神灵及其运作模式的象征表达。根据史禄国的介绍,在后贝加尔的通古斯人中,萨满分别有进入宇宙上界和下界的神服,萨满仪式过程中各种器具象征着萨满旅行过程中的一些神灵助手和工具等。在社会地位方面,萨满在氏族生活中没有什么权力, 他们一直受到氏族成员公众意见的检验和评判。 萨满在通古斯人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有的萨满擅长萨满教“理论”,有的萨满擅长歌唱和舞蹈,有的萨满擅长治疗和占卜。
四

在对“心智丛”的理论说明中,史禄国认为它是不断变迁的。史禄国将这个过程分为两种类型:“变动的平衡”以及“失衡”。这种变动的动力可能来自于族群内部的变化(主要是人口数量的变化),也可能来自于族际间的压力,一个僵化的 “心智丛”可能会对族群单位一般的反映功能造成障碍。史禄国认为,我们可以“把族群文化认知作为理解“心智丛”状况的基础问题”[1]412,族群单位对 “心智丛”的变化包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拒绝, 人们会拒绝一些文化要素(尤其是在有书写系统的族群单位中更倾向于发生拒绝的现象),人们也可能凭借直觉猜想而接受一些文化要素,出于再适应的需求接受一些文化要素,“心智丛”的这种管理,确保族群单位以特定的速度运行,同时与文化适应的其它要素变化过程相对应。

不过,“心智丛”也可能发生失衡的现象,这是指“心智丛”不能满足族群单位对环境必要的认知需求,以及以此建立起来的保证族群运作单位的知识。在族群所依托的基本环境、派生环境以及族际间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心智丛” 的失衡现象。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由于迁徙而发生的环境改变;由于战争产生的思维能力的改变;食物的缺乏;人口的减少;领土的增加或者减少等等。史禄国认为,“在族群单位的生命中, 由于族际压力而产生的失衡现象要比内部影响更加普遍”[1]410。外来族群的压力可能会通过文化要素的引进来表现,他认为这些要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心智丛”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族群单位变迁速度加快的情况下。
史禄国结合通古斯人的具体社会历史对萨满教文化丛产生以及功能做出解释。他认为,“通古斯人对佛教文化的引进导致了精神紊乱的增加, 佛教传遍了整个通古斯人那里,集体或者个人的心智紊乱是对这一观念引进的反映”[1]414。他认为萨满教文化丛是族群单位“心智丛”在面临失衡危险时而引发的一种自我管理的实践。“从萨满教本身来理解萨满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对说明萨满教的功能毫无帮助”[1]415。他认为,萨满教的产生与佛教传入后通古斯人祖先中发生的个人和大众的精神紊乱有关,作为一个派生性的文化丛,它源自于通古斯人一个长时间的对“心智丛”进行自我管理的过程,它的主要功能在于管理族群成员的心智生活。萨满教是通古斯人“心智丛”不稳定时,进行自我管理的一部分,这种不稳定由族际压力产生,族群单位采用萨满教是出于族群“内部” 应用的目的。
史禄国分析,在面对族群“心智丛”失衡的危险时,通古斯人将为“心智丛”带来困扰的要素用神灵进行象征表达,并由具有控制“神灵”能力的萨满通过仪式的手段对心智失衡状况进行调整。 萨满处理的“病人”并非是病理学意义上的患病, 他们的“病”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的, 因而也需要通过族群自身发育出来的“萨满教”进行治疗。萨满一般是在氏族内部或者地域内部产生,他们的治疗依据对氏族神灵的基本假设和掌控,治疗的方式则多是个人性或集体性的仪式。
在对仪式作用的分析上,史禄国采用了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正像他所言:“民族志研究者对心理学方法的运用针对民族志工作的某些方面,它只是一种普通的方法,不能将其滥用。”[1]8他对萨满治疗的分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如萨满在治疗中对非逻辑思维、直觉、暗示等方法的运用,以达到仪式的心理治疗目的。
总之,史禄国的萨满教研究是在通古斯人自身的文化语境下展开的,它连接了通古斯人的历史与现实,将通古斯人萨满教文化丛放在与其相关的其它文化丛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理解,并将其还原为心智层面的文化现象,从历史与功能的维度进行观照,开创了民族学视野下的萨满教研究传统。与史禄国萨满教研究成果、观点的反思性对话,笔者将有另文探讨,故不在此赘述。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欢迎投稿

栏目主编的邮箱:
yunafk929@163.com
公号公共邮箱:
folklore_forum@126.com
(这个邮箱请注明新青年)
文章来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02期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拓展阅读
66.新青年 | 罗士泂:物的社会生命:徽墨的社会史研究——基于个案的历史分析
65.新青年 | 谷子瑞:变与不变:技术世界中的定州秧歌 谷子瑞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