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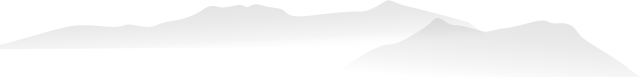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胡建升,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在新世纪之初,文学人类学提出Big Tradition的文化理论,全新改造了欧美人类学家的Great Tradition,彰显了史前无文字时期的华夏智慧与文化源头,重视以史前之物为实证的隐蔽秩序与文化文本,强调史前人类文化的神话原型与文化结构功能,对重新发现华夏文明精神具有本土知识引领作用。
中西文化大传统理论的比较研究
胡建升
原文发表于《文学人类学研究》
2019年总第一辑
摘要:欧美人类学家提出的Great Tradition是西方文字中心主义、意识中心主义、精英文化主义的具体表现。在新世纪之初,文学人类学提出Big Tradition的文化理论,全新改造了欧美人类学家的Great Tradition,彰显了史前无文字时期的华夏智慧与文化源头,重视以史前之物为实证的隐蔽秩序与文化文本,强调史前人类文化的神话原型与文化结构功能,对重新发现华夏文明精神具有本土知识引领作用。
关键词:文学人类学;文化文本;Big Tradition;Great Tradition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1956年出版了《乡村社会和文化:走进文明的人类学方法》,在此书中,他提出了欧美文化的大小传统理论(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其Great Tradition指代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家在学校与寺庙之中传播的文字书写传统,是小众文人的反思传统。其Little Tradition指代乡民在乡村流行的口头文化传统,是大部分乡民的非反思传统。[1]近年来,叶舒宪对欧美人类学家的大小传统作了全新的文化改造,其云:“有必要从反方向上改造雷德菲尔德的概念,按照符号学的分类指标来重新审视文化传统,将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做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2]文学人类学的大传统(Big Tradition)是指史前无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其小传统是指文字出现以后的文化传统。

原名: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中国文学人类学结合本土文化的精神特质,改造了西方学术界流行的Great Tradition,提出了富有本土文化意义的Big Tradition,对于重新发掘华夏文明起源与文化智慧具有不可限量的意义。在欧美文化Great Tradition的表述中,Great具有“伟大”、“精英”的文化赞许意味,属于“high culture”(高等文化,与之相对的是low culture低等文化)、“classic culture”(经典文化,与之相对的是folk culture民间文化)或“learned culture”(博学文化,与之相对的是popular culture流行文化)[3],具有西方理性意识的二元对立判断意味。在文学人类学的Big Tradition中,Big具有“无限”、“无有”、“极大”、“极久”等方面的文化意味,具有现代文化寻根、无意识统一的神话象征意味。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值得讨论。
一、Great Tradition的文化自大情结:
文字文本
雷德菲尔德用Great Tradition指代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是hierarchic culture(等级文化,与之相对的是lay culture混沌文化)[4],充满对史后精英文化的肯定与期许,很容易形成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二元结构对立。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中,余英时接受了美国人类学家的文化大小传统观念,其云:“在五十年代以后,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之说曾经风行一时,至今尚未完全消失。不过在最近的西方史学界,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观念已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名词尽管不同,实质的分别却不甚大。大体来说,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中国文化很早出现了‘雅’和‘俗’的两个层次,恰好相当于上述的大、小传统或两种文化的分野。” [5]余英时将欧美人类学家的大小传统机械地移植在汉代士人文化之中,将其直接转换成为“雅文化”与“俗文化”两个文化层次,突出了精英文化的优越性与高等性,将小传统贬谪为“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民间俗文化传统。通过文化传统概念的机械转移,他也将欧美人类学的文化偏见直接引入汉代士人文化的讨论之中。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在此,我们结合中国学者运用Great Tradition的文化阐释,来总括Great Tradition的文化表征。具体说来,其文化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Great Tradition的时间指向倾向于人类史后的时间维度。作为经验直觉的时间存在,有着过去、现在、未来的持存性与延续性,尤其作为自然时间的历史延绵,后来的时间存在不仅从前面的时间之中生发延伸出来,而且将曾在的历史经验与生命能量也转化为现在的时间存在,在历史时间存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并不存在生命能量的文化差异。如果将史后的文化传统称为Great Tradition,在时间维度上,就会过分放大史后时间的生命存在与能量价值,就很容易导致对生命原初时间与生命能量的忽略与排斥,从而造成时间历程的文化冲突。将Great Tradition的时间观念移植到东方文化阐释中,就会将史后的人文价值作为华夏文化的起源时间。如戴茂堂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本结构与当代建构》中云:“中国价值观念的大传统发端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流派迭出,学术繁荣,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价值观念大传统的基础。”[6]他将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当成是华夏文化的大传统,彰显了史后轴心时代的文化价值,这种大传统的文化判断就会误导学人,使人片面认为,史后的精英文化才是华夏精神价值的原初价值所在,而这种西方文化大传统观念的历史时间局限,恰恰成为工业文明时代文化危机的症结所在。
Great Tradition的表述载体形式直接指向了文字文本。人类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化的一大创造,体现了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巨大进步,但是如果过分夸大文字的奇效作用,就会忽略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已经存在极为久远的口传说话历史,在这段久远的口传文化历程中,人类已经通过各种表述形式创造了自身文化的独特精神。人类发明了文字符号,并非意味着人类的文化精神就彻底抛弃了无文字时期的精神遗产。后起的作为载体形式的文字符号,起初只是作为辅助性的传播工具,的确为人类文化的记忆与保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文字作为有形存在之物,它天生就与无形的文化精神是相背离的。用文字形式作为无形精神的替代之物,它就始终以有形存在之物的方式,站在了无形精神的前面,展示出文字文本的绝对优先性。这种有形之物的优先性意味着,文字具有一种天生的两面性:一是作为无形精神的替代之物,二是作为无形精神的取代之物。作为前者的文字形式依旧是无形精神的辅助性存在形式,作为后者的文字形式就不甘于成为他者的辅助形式,而是要以自身的有形存在来取代无形精神的优先存在。可见,文字文本作为一种表述的载体形式,文字的符号意义就可能会遮蔽作为象征意义的文字功能。学术界机械移植西方文化的Great Tradition,也会将文字自大的文化情结移植过来,造成对华夏文化的片面理解。戴茂堂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本结构与当代建构》中云:“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之层级差别体现为中国价值观念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其中,中国价值观念的大传统是指经过思想家加工定型后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作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它对应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阶层和统治阶层;而中国价值观念的小传统是指不定型的、以口头相传等方式表达出来的、作为潜意识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对应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贫苦大众阶层。”[7]他以文字作为中国传统价值的文化大传统,将口头相传定为小传统,尤其将大传统限制在“统治者”所倡导的文字文本与意识形态之中,极不利于发现华夏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尤其容易忽视华夏文化重视人民、尊重人民的文化本位观念。
Great Tradition的文化主体主要集中在精英层面。精英文化的主体成员有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家、理论家等等,他们以识字为文化基础,以读书为文化身份,形成了一个以书写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集团。这个以书写为技艺的文化集团,重视书写符号的有形存在,强调书写知识的重要性,相对于那种没有书写文本的口传文化,天生就抱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对其他的无文字的文化表述形式抱有一种视而不见的贬值态度,这种文字自大与傲慢的文化态度就自然会形成知识阶层的分层与分裂,尤其会导致文字载体形式对其他表述形式的拒绝与否认,一种文字文本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就会得到极度夸大。戴茂堂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本结构与当代建构》云:“主张中国价值观念大传统的人骨子里往往趋向小传统,而主张中国价值观念小传统的人实际上却又无时不流露出对大传统的敬仰与认同。”[8]他认为,精英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在社会中具有重大的价值引领作用,体现出了精英文化的自大与狂妄,这种文化片面态度就忘记了华夏文化真正的精英传统始终都是扎根民众的,而不是让民众唯精英文化是瞻。
Great Tradition的文化精神过分强调人类的意识意义。人类心理是从无意识逐渐发现意识之光的,从一开始,人类极度沉浸在无意识之中,产生了对无意识黑暗的恐惧情结,同时,随着人类理性意识的浮现,人类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手段来维护意识理性的微弱光明,理性意识逐渐成为人类心理的积极能量,无意识成为人类心理的阴影,意识理性总是表现出压抑、排挤无意识的存在。但人类意识天生就是从无意识之中产生的,意识理性的光明只有在无意识的无尽混沌中,才能显现出自身本能的光明,所以意识尖角的光明始终都是在无意识之中才能体现出来的,才能获得无意识混沌之中源源不断、无尽能量的传输与保障。如果因为片面强调人类意识的重要性,而导致极大忽略意识理性的根源问题,就会导致人类心理根部与枝叶之间的隔离与断层,也会导致人类意识的狭隘偏见。在Great Tradition这种意识自大的文化价值基础上,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唯意识论的大传统文化幻觉。蒲娇在《民间庙会稳态性研究》中云:“大传统在国家体制、官僚组织等社会秩序及伦理道德的关系方面十分注重,并对分辨儒释道的派别及产生源流等问题非常严谨。但在小传统乡民的世界中,他们并不能按大传统的意图来理解这种复杂体系。当然,这不能妨碍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许这种方式只是一种狭隘世观的体现。”[9]在欧美大小传统观念的支撑下,作者将中国社会的儒释道文化定为大传统,将乡民的文化世界定为小传统,并认为大传统的品格在于“严谨”,而小传统的方式极为“狭隘”。这种唯意识形态的大传统观念就表现的极为明显。
由于欧美人类学家所提倡的Great Tradition过分倚重文字书写,强调人类精英的意识理性,就自然会排斥人类其他的各种表述形式,极大地缩小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相关阈限,也会扭曲华夏文化精神的合理结构,形成文字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与精英中心主义的文化不足。只有摆脱欧美人类学Great Tradition的狭隘视野与唯理思维模式,才能积极拓展人类知识生产的文化新视野与发生新模式,文学人类学有鉴于此,结合华夏本土文化的质性特征,提出了全新的Big Tradition理论。
二、Big Tradition的文化再启航:
文化文本
中国文学人类学经历三十余年的本土文化破译以及华夏文明探源,牢牢把握住了华夏文化精神的生成质性与延续模式,结合符号学的生成传播结构,适时提出了Big Tradition 的文化理论,既突破了西方人类学家理性认知中心主义的文化拘囿,又彰显了史前无文字时期的文化原型意义,重视从无文字时期到文字时期的文化传播价值。文学人类学的Big Tradition文化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转型。
Big Tradition的时间重心指向了史前历史。人类史前时期的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的时间临界点是可以无限拉伸的,Big Tradition 与Big History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史前时间的长度与厚度成为Big Tradition与Big History关注的文化重心。当史前时间成为文化研究的重心时,人类的史前存在与文化遗存问题,就开始成为史后文化研究的基础价值。只有揭开史前文化的谜底,才能梳理史后文字文本的生成条件,以及重译史后文字书写的原初编码。人类存在的时间观念,就由Great Tradition的发展时态,变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融时态。过去可以为现在、未来提供一种知识的预期可能,过去就能在人类集体命运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现在与未来都是过去经验的文化积淀。
Big Tradition的表述载体形式由文字文本转向了文化文本。从发生时间来看,史前文化文本是史前无文字时期的人类表述形式,它先于文字文本而优先存在,史前文化文本的优先条件性决定了文化文本作为史后文字文本的意义基底存在。文化文本的重心在于探讨文化精神,文本形式不过是依附于文化精神的表层载体,文化精神成为文本形式的核心根据。与文化文本的物质意象形式优先相比,文字文本是以文字形式作为优先条件的,两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文字文本在文字替代的过程中,就开始出现文字霸权的权力关系问题。首先,文化文本是对文字文本的形式解构,这种形式解构行为不是对文字形式的完全抛弃,而是一种暂时的扬弃。通过先扬弃文字文本,才能获得建构起文化文本及其原初意义的机会,才能有效地释放出被文字文本所压抑的、处于潜藏状态的文化精神。其次,文化文本是对原初精神意义的文化建构,重点彰显人类原初文化的精神存在与理念现象。叶舒宪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一文中认为:“再造大传统的概念,针对的就是认为文字创造了历史、无文字就是无历史的传统偏见。我们承认文字历史只是小传统的历史,要看到前文字时代更加深远的历史,则需要探寻大传统的存在。”[10]其《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又云:“不突破文字小传统的成见束缚,就难以看到大传统的真实存在。”[11]史前文化文本是前文字时代的物质图像表述形式,Big Tradition是以破除文字偏见为起点,然后利用前历史时代的物质物象意义,来重新启航文字书写的小传统文化。
Big Tradition的表述主体主要是原型主体。原型主体与一般意义的意识主体不同。原型主体是通达了人类心灵的原型状态的主体,而一般意义的意识主体主要是理性主体,即遮蔽了原型主体的理性主体。主体意识是人类理性的心理表征,人类理性极大地张扬了个人的主体价值,膨胀了人的意念欲望,人类理性重视主客之间的分别,始终将主体之人作为宇宙的中心,就忘记了自然宇宙的生命价值,也遮蔽了在客体之上的原型意象。原型主体尽管还是人的存在,但不是人的工业理性存在,而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无意识到意识的过渡阶段,是无意识-意识的整体交融状态,原型主体的主要特征是“神人合一”。“神性”指代人类心灵的无意识状态,是人性的文化基底与行动根据,“人性”指代人类无意识之中发出的意识之光,是以“神性”之光为心理基础,人性意识的发展是从神性中获得了原初的能量支撑。结合华夏文化的精神价值,原型主体就是一种“真人”、“至人”、“神人”、“圣人”的心性结构与本真存在,承载着厚实混沌的文化基底,与一般意义的理性主体存在很大差异。叶舒宪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中云:“中国8000年就开启了‘玉器时代’,圣人也正是在这个大传统中的产物。”“圣人”就是原型主体在世界之中的个体表现。其《从玉教神话观看儒道思想的巫术根源》云:“儒道两家所出现的春秋时代显然属于汉字使用后近千年的文化小传统。分析儒道两家创始人老子和孔子的言论,有望找出在分歧对立表象后面的同源同根特性:圣人(圣王)崇拜与圣物(玉石)崇拜。圣人与圣物的对应现象由来已久,大约要比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时代早2000多年。”[13]“圣人”是原型主体,“圣物”是原型客体,是原型主体的无意识状态在客体层面的投射结果,“圣人”与“圣物”都是具有一定神秘质性与意象形态的有形载体,强调的都是主客浑然一体的整体结构。
Big Tradition极为重视神话原型的文化意义。人类理性的综合判断总是依据人类理性而进行的推理与演绎,过分倚重和张扬人类理性的统觉整合作用,这种理性中心主义的最终认知结果就经常会呈现出理性统一与经验事实的实际背离。神话原型的文化意义也离不开人类心理的统觉作用,但是这种文化统觉不是纯粹理性统觉,而是直观想象的投射统觉,是一种直觉经验与心理无意识的有机结合,是自身集体无意识的生命能量与自然客体世界的神明幽灵之间的一拍即合,或称之为目击道存式的统觉作用。神话原型一方面依靠人类的直观统觉作用,借助对象的有形形式,生产并获得一种神话意象。另一方面它又是集体表象与神明参与的直观统觉,两者自然融合,我们很难分清主体与客体、意象与对象、心理与世界之间的明显界限。正是神话原型的有机融合,才可以避免人类理性的片面自大,同时,又可以沟通人类心灵的集体无意识与宇宙世界的幽灵神明之间的同步同质同位关系,既是神秘渗透的结果,也是内外贯通的统一,是一种现代科学还没有产生之前的“大科学”状态。发掘并阐释这种“大科学”的文化状态与集体想象,才是Big Tradition的关注重点与文化贡献。
三、Big Tradition的原型编码:
史前原型对神话历史的再建构
文学人类学提出Big Tradition的文化理论,直面了华夏文化发生的最初源头,将人类理性的反思推向了理性萌发之初的临界点。叶舒宪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云:“从文明史的角度判断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有一个容易辨识的基本分界,那就是汉字书写系统的有无。如此以符号分类为标准的划分,将有助于当今知识人跳出小传统熏陶所造成的认知局限,充分意识到传统是历史延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并由此透过文字小传统的习惯性遮蔽,洞悉文化大传统的原型编码作用。”[14]文学人类学的Big Tradition将学术目标定位为发现和重建华夏大传统文化的原型编码,希望利用史前文化文本重讲中国故事,再建华夏文明早期的神话历史。

《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 叶舒宪
Big Tradition重视史前无文字时期的文化传统与文脉精神,将文化意义的追寻诉求于出土的史前文化之物。百余年来,考古学的迅速发展,使文化研究获得了大量的以文化遗址与史前遗物为主体的文化文本,这些考古出土的新材料极大丰富了史前人类的历史文化,也为Big Tradition的神话历史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考古出土的史前之物成为Big Tradition重新认知华夏史前文明与文化精神的首要证据,也是文学人类学重审华夏文明起源的新起点。一方面大量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历史事实开始浮出水面,如史前玉石神话,良渚神徽,神木石茆古国,三星堆青铜文化,都将成为Big Tradition文化理论开疆拓土的重点,也为建构史前文化文本的原初意义提供全新的出土实物证据。另一方面传世文献中关于史前历史文化的零星记载,在考古出土的遗物与遗迹中,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新证据,依据出土的物质图像,结合口传文化、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综合考察,整体释古,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为解开史后文字书写的重重疑团提供新路径,这也将成为重译华夏文化精神与神话历史的新起点。在文学人类学倡导的四重证据中,物质图像证据虽然是最后提出的,却是最为重要的文化文本,成为最为有效的物质铁证,与口传证据、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其他三重证据相比,具有物证如山、以物服人的优先意味。叶舒宪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云:“大传统的存在,需要借助非文字符号的研究和重构,主要的非文字符号来自考古学的实物发掘。”[15]史前无文字时期,华夏文明尽管还没有发明文字符号,但华夏先民已经开始运用物质、物象的文化方式,表达与传播人类原初的心灵意象与文化意义。我们利用考古出土的史前实物与神话图像,可以重新打捞人类先民的原初思维与神话意象,以及探究在这些神话意象背后所潜藏的人类心灵结构与神话原型。
Big Tradition发现了华夏史前核心文化的神话基因与物质原型,即史前玉石神话信仰。玉器与玉礼器先于文字出现在史前文化时期,成为华夏早期文化的原初基因。叶舒宪将史前玉石文化的特殊形式以及玉石神话信仰称之为“玉教”。“玉教”的发现与提出,对于重新认知华夏文明起源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玉教”发端于距今8000多年的兴隆洼文化,随着史前玉教的神话信仰与物质符号在华夏文明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四处传播,极大彰显了史前“玉教”的神话信仰在华夏史前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在距今5000年前后,从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再到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玉器神话信仰是华夏文明在史前国家政治统一之前,就已经遍布了华夏文明的各个角落,具有玉石文化统一中国的文化先声与信仰现象。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在史前文化的文明之初,就已经将华夏精神表现在玉石文化共同体的神话信仰之中,玉石神话信仰在史前中国的文化统一,就已经昭示了一个即将统一的华夏民族国家的政治可能。玉石神话信仰从史前到史后,都成为华夏文化精神中人心凝聚、族群建构和国家团结的核心符号与精神力量。
从史前遍地开花的玉石神话信仰中,我们就可以窥探出华夏史前精神的文化底蕴与基本价值,而这种玉石文化不是文字文本的符号形式存在,而是纯粹的无文字的物质符号与文化文本。这种以玉石物质为符号核心的文化文本,在文字文本出现之前,就已经建构起了华夏史前人类的心灵世界与文化价值的统一结构。史前玉石物质的文化文本,与儒家文字文本的“君子比德于玉”,以及道家文字文本的圣人“被褐怀玉”,都要早3000余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前玉石物质神话的文化文本才是华夏文化精神的根基所在,而道家与儒家对玉文化的文字文本书写,只能算是华夏史前神玉信仰在文字出现之后的金枝玉叶。
Big Tradition不仅发现了史前玉石神话信仰的原型编码意义,同时,还依据玉石神话信仰的原型编码来重新译解各种历史书写的意义编码,由此而提出了大传统的N级编码理论,强调史前原型编码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历时贯通作用。
叶舒宪在《N级编码:文化的历史符号学》中云:“从大传统到小传统,可以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出N级的符号编码程序。无文字时代的文物与图像,有着文化意义的原型编码作用,可称为一级编码,主宰着这一编码的基本原则是神话思维。其次是汉字的形成,可称为二级编码或次级编码。……三级编码指早先用汉字书写下来的古代经典。……今日的作家写作,无疑是处在这一历史编码程序的顶端,我们统称之为N级编码。”[16]在N级编码理论中,史前的神话原型是一级编码,甲金文是二级编码,儒家经典与战国时期文献是三级编码,秦汉以后至现当代的各种书写文本属于N级编码。以前的学术界,由于过分重视各个历史阶段文化的推进演化,注重文本书写的异质特性,就忽略了史前华夏文化的精神基底与神话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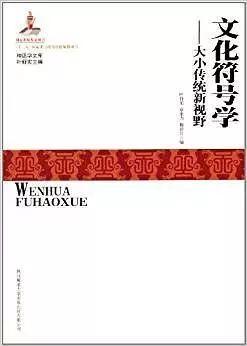
《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 叶舒宪,章米力,柳倩月编
文学人类学Big Tradition的N级编码犹如解开人类身体秘密的遗传基因一样,揭开了史前文化基因在文化传承延续中的稳定因素与遗传特性。原型编码的文化遗传从史前贯通于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可限量的自然生命力。史前文化原型的基因作用以一种不可人控的神奇状态,体现在历史不同时期的各种书写文本中,尤其史前文化的基因编码也突显了华夏精神的原型同质与文脉血缘。
余论:
Big Tradition的诗意遐思
与自然科学的理性沉思不同,文学人类学的Big Tradition要开启的是人类文明之初的诗意遐思。在原初人类的诗意遐思之中,各种神话意象纷呈而出,姿态万千,任意组合,尽是奇幻之境,这种神话意象在考古出土文物中表现极为明显。
这种神话意象不是物质对象的机械模仿。外在的物质对象能够引发、刺激人的文化遐思,但是遐思意象却不是对象,而是在主体无意识之中就已经存在的文化遗产,它应时而出,应机而成。对象只是一个现实的事件机缘,它引发了初人的诗意遐思,令人浮想联翩,激发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幽眇之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神话大象依附在对象之上,对象因此而获得了超越客体的幽灵存在。
这种神话意象不是语词的固态规则。语词的运动是一种人类理性元语法的声音之流。语词作为对象的替代之物,不是对象的科学表征,而是自身语法规则的叠床架屋。遐思意象与语法之中的语词之流不太一样,它没有固定的语法规则,也没有完整统一的语法成分,它只是一些不断从心灵深处跳跃而出的象征符号。当各种各样的象征意象以不知所措的形式蜂拥而出的时候,遐思主体只有沉醉的迷茫,与不知所措的行动,却丝毫也没有清醒的意识认知。象征意象对Great Tradition的语法规则具有全面解构的文化批判,它所呈现的是海面孤岛的起伏跌宕,呈现的是一幅充满诗意、幽深迷人的人文景象。
这种神话意象不是理性的逻辑思维。理性逻辑在零散浮动、浮光掠影的神话意象面前,表现出河伯初见大海般的“望洋兴叹”与无奈心情。理性意识的自大与傲慢,在没有涯际的大海面前,顿然消失的无影无踪,理性又一次回归到人类和平的心灵之中。当理性意识回归到诗意的神话遐思之中时,当小传统文字书写回归到人类大传统的心灵怀抱时,一股自然而涌的心田暖流将会洋溢而出,诗性生命又将勃发生机。理性之河,终归大海。Big Tradition将工业文明的理性河伯纳入大海,百川归海,生命之水又在萌动,即将开启新的神话循环历程。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文学人类学研究》2019年总第一辑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拓展阅读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